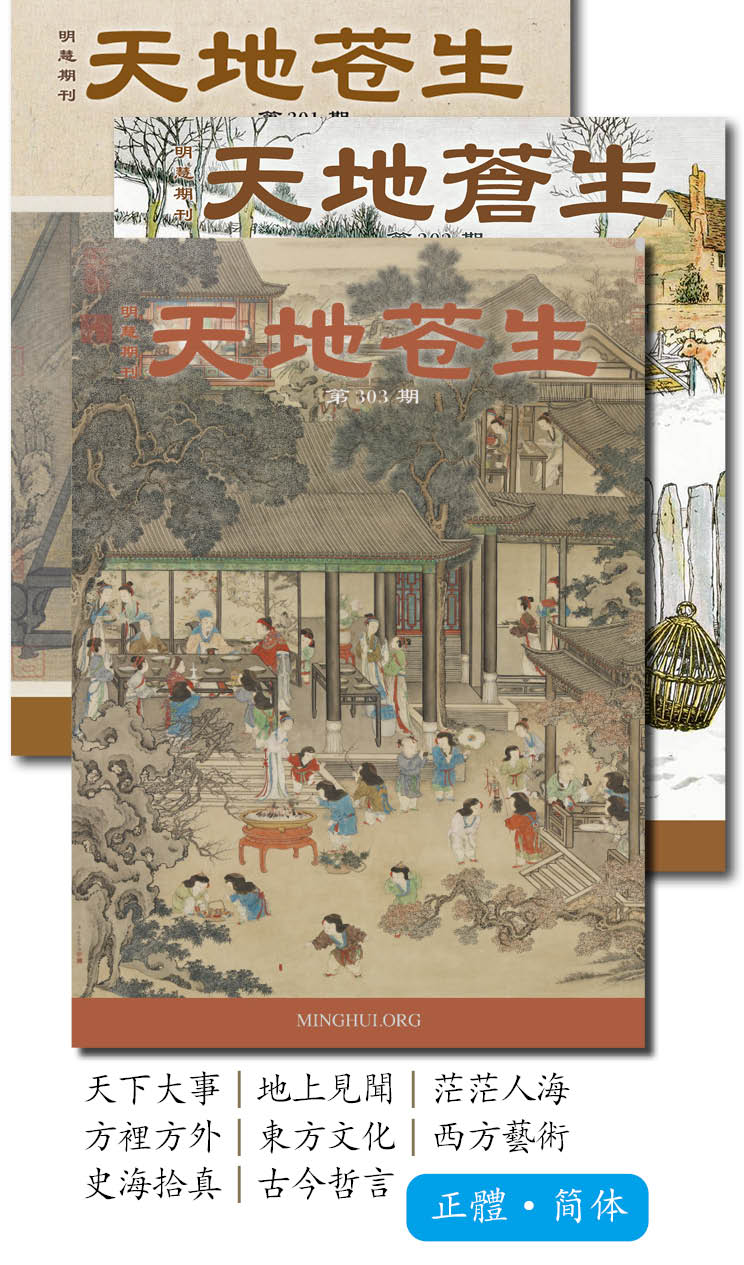北京青年魏張同控告元凶江澤民
現年二十一歲的魏張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以下是魏張同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的父母魏學軍、張秋莎開始修煉法輪功,並按照法輪功教導的「真善忍」理念做人,身心得到了巨大改善。父親魏學軍戒掉了煙、酒和麻將等不良嗜好,媽媽張秋莎也不爭強好勝了,遇事儘量為別人著想,身體的疾病不知不覺中都好了,此後十六年來,父母沒吃過藥,但身體健康。
我從小有鼻竇炎,經常憋得哭,喝口服液、往鼻子裏噴藥都不管事,大夫說只能長大後做手術。父母開始修煉法輪功時我五歲,我只是隨父母去煉功點玩兒,一個月後我的鼻竇炎竟好了,再不用喝藥和噴藥了,也沒去做手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迫害法輪功,我全家及親屬深受其害。當地「六一零」辦公室、公安機關對我家非法抄家,父親魏學軍、母親張秋莎各被非法拘留五次,給我家庭和我的成長過程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父母帶我去北京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被北京警察綁架,父母後被非法拘留。我當時五歲,從沒離開過媽媽,每天想媽媽很痛苦,在奶奶家數著手指頭盼著媽媽回家。奶奶身體虛弱多病,每天唉聲嘆氣,大把大把的吃藥。爺爺在單位擔任領導工作也覺得抬不起頭來,曾一度得了抑鬱症。
二零零零年一月,父親魏學軍去天安門請願被行政拘留十五天,關到大興拘留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的一天早晨下著雪,媽媽帶著我出去煉功,被大興清源派出所警察強抓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我見到被大興清源派出所警察剛剛從大興拘留所接到派出所的爸爸。我和爸爸被爺爺接回家。媽媽被大興公安局警察劫持到大興拘留所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父母在大興區安定鄉一同修家被安定鄉派出所警察綁架,之後被劫持到大興拘留所非法關押一個月,我只好跟爺爺奶奶生活。爺爺和奶奶經常掉眼淚,覺得日子沒法過了。
二零零一年五月,大興公安局警察闖到我家非法抄家,並把我媽媽抓走,非法拘留一個月。
二零零一年六月,因父親堅持修煉法輪功,他的工作單位解除了勞動合同。我家沒有了經濟來源,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很困難,家裏的蔬菜就是白菜和土豆。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早晨,父親去煉功點煉功,被清源派出所警察綁架,後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二年上學期的一天,黃村鎮派出所兩名警察闖到我的學校大興七小,把八歲的我帶到校長辦公室盤問,問我是否煉功,問我家裏人員情況,問我父母都和誰來往等等,盤問了一個多小時。黃村鎮派出所警察王尊亭還經常去我家騷擾,給我家貼封條、斷電等。一天中午放學,王尊亭尾隨我回家,以土匪的姿態對我媽媽說:「告訴你,給你打電話就得接,叫你去派出所就得去,來你家就得給開門,不開門就呲門斷電。」並強行把我母親帶到黃村鎮派出所,罰站半天後才被爺爺接回家。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下午,王尊亭夥同另外一名警察,又尾隨我放學闖進我家。將我媽媽劫持到洗腦班。八歲的我由姥姥每天接送,我怕同學嘲笑媽媽被警察抓,放學時經常在同學面前故意大聲問姥姥:姥姥,我媽忙讓你來接我了,是吧?
二零零四年,媽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大興華堂商場服務台的工作,大興公安局的三名警察找到工作場所騷擾她,盤問還煉不煉法輪功及家庭情況。媽媽怕被再次綁架,只好放棄這份工作。當時很多單位都不敢用煉法輪功的人,怕給單位找麻煩。媽媽能找到的工作都是離家遠、掙錢少還特別累的私企工作。即使這樣,迫於轄區警察的騷擾、社會上的壓力還要經常換工作、換手機和卡號,社保也無法保障。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媽媽被北京市公安局巡邏警查車,因車內有真相手機,被綁架至大興公安局興豐派出所審問。晚上十二點後,大興公安局國保大隊、興豐派出所警察近十人闖去我家非法查抄,並把在家睡覺的父親魏學軍也抓走了。我父母被非法拘留了一個月。我家的豐田車和我的電腦等私人財物,警察至今不還。
經歷了數次父母被抓,年幼的我既恐懼又怕同學恥笑,無法安心學習,從此不愛上學也不愛學習。失去了正常的成長環境,天天提心吊膽,甚至有人敲門都害怕,每天高度緊張,生活在恐懼當中,怕外面看到家裏有人,自己的小屋從來不敢開燈。五歲到二十一歲,我在高壓、歧視、貧困、擔驚受怕中成長,甚至不知道正常家庭的生活,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影響了學業和整個人生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