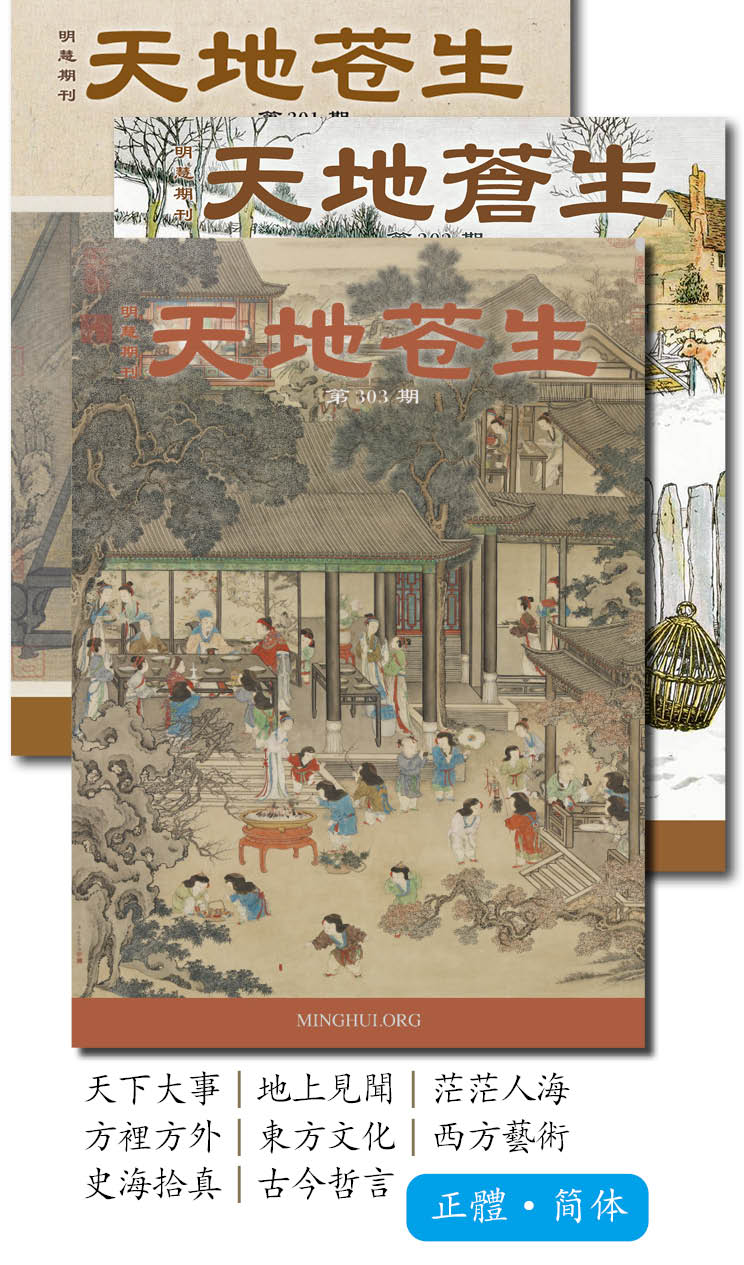兩次遭非法勞教 內蒙古盧洪偉控告江澤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後,改變了盧洪偉擁有的這美好的一切。她自己本人遭非法勞教兩次,九死一生。家庭經濟損失很大,家庭破裂,兒女們精神上遭受巨大創傷,幸福的家不復存在。盧洪偉現在控告發動這場迫害的江澤民,她說:「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就是江澤民集團的迫害,罪魁禍首當屬江澤民,我強烈要求對被江澤民予以立案偵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並予以法律制裁!」
以下是盧洪偉在控告書中陳述的被迫害情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我被強行關押至翁旗黨校洗腦班七天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因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綁架,帶到內蒙古赤峰市駐京辦事處,後被翁旗國保大隊帶回關押至翁旗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和幾個法輪功學員一起煉功時被看守看見,對我們拳打腳踢,並用串著鑰匙的鐵圈猛打我的頭部,之後把我拽到刑訊室繼續毆打;隨後到我家抄家,甚麼也沒搜到氣急敗壞的一連打了我六個嘴巴。之後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八日,我被送往內蒙古圖牧吉勞教所勞教三年。
在圖牧吉勞教所,白天天一亮就出工上山幹農活,晚上頂著星星回到勞教所後又要被強行轉化,整宿不讓睡覺、罰站,戴上手銬拳打腳踢,而且還有兩個包夾二十四小時監控,不許與人正常交流。包夾為了所謂的「減期」誘惑,無所顧忌的無中生有加害於我。
有一次為了應對所謂的轉化率,把我關進禁閉室,寫了假轉化書強行讓我按手印,我要求見大隊長,他們不准,於是我就絕食反迫害,他們就給我灌食,抓住手腳不讓我動,然後一個男隊長用鐵棍撬我的嘴,直到把下門牙撬掉兩顆,滿嘴是血才住手(由於這個原因,現在滿嘴牙掉的只剩下幾顆了。)。然後,又強行扒掉我的外衣,把我帶回宿舍用手銬吊到床頭,一個大隊長進來還羞辱我!
 |
還有一次夜間,我被電棍聲驚醒,起來一看是在電我下鋪的一個法輪功學員,於是我大聲制止這種迫害行為,誰知那個隊長惱羞成怒,拎著電棍便朝我頭上電來。這時整個宿舍的人都驚醒了,和我一個宿舍的一共五名學員,另三個也起來制止迫害,當時我的腦袋被電的出血了,嚇得那幾個刑事犯也哭喊著隊長不要電了。他們把其他四個法輪功學員銬在走廊暖氣管上,然後又讓幾個包夾按住我仰面朝上,拿著三百六十伏的電棍電我,並用穿著皮鞋的腳往我胸口使勁踹,再把我翻過來掀起衣服電後背,又用腳踹臀部,嘴裏還罵聲不斷:看你還管閒事。其他的隊長又到走廊去電另外四個法輪功學員,電棍沒電了就充上電繼續。這樣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她們筋疲力盡才罷手直接送我到地裏幹農活!中午收工後躺在床上,渾身像過電流似的直哆嗦,胸部和尾椎骨處鑽心的疼痛,學員們難過的看著我直掉眼淚,我整整昏睡了一下午。即使這樣,第二天我照樣被帶出去幹農活,我渾身無力,晚上收工時一個隊長故意讓我一個人扛一大盤澆地用的塑料管,我根本就拿不動,於是這個隊長一邊罵一邊用腳踢我小腿骨,直痛的我打哆嗦!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從勞教所回到家裏。這三年來,丈夫因為要照顧兩個上學的孩子,又要照顧生意,還要為我的事情奔波,就顧不過來,結果本來十分紅火的生意黃了;兒子在學校裏有同學知道媽媽勞教而被歧視不堪打擊而輟學;女兒由於想媽媽每天不語。
二零零五年一月,警察闖入家裏搜出大法書後,又把我綁架到翁旗看守所,幾天後又轉入赤峰市松山區看守所,我絕食反迫害要求間所長並告訴他:明辨是非,不要當替罪羊。第二天就又被轉回翁旗看守所。在翁旗看守所我繼續絕食反迫害,便被強行下胃管,那種滋味真是十分痛苦。過完新年就被送到內蒙古呼市女子勞教所勞教三年。
由於我一直絕食,身體十分虛弱,到呼市勞教所後體檢時測不出血壓、心跳不穩,勞教所拒收。但是送我的一行人並不死心,在旅店住下第二天托關係硬是把我送進勞教所。
在呼市勞教所,除每天超負荷的勞動外,還要經常被「洗腦」,強迫看污衊師父和大法的錄像。有一次我因為向隊長反應勞動超負荷的問題被隊長在大會上辱罵一頓。
二零零八年回家時,滿目荒涼:院子裏是半人高的雜草,窗台上厚厚的灰塵;因為這幾年丈夫不堪家庭重負和警察無休止的騷擾已離家出走,孩子們被丈夫寄居在親戚家裏,只剩下沒有人煙的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