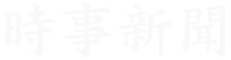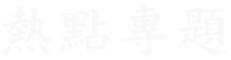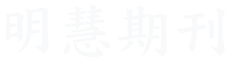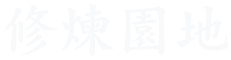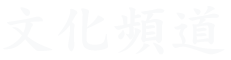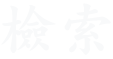信師信法 走出魔難
二零一九年七月的一天,我們幾位同修約好上午下鄉發資料。不料原本晴朗的天下起了大雨,等到雨停了要出發時,三輪車鎖裏進水了,晾乾車鎖出發,到達村屯邊時,車胎又沒了氣。出現的這些干擾其實是師父在提醒我們心性有問題了,應該向內找自己。但在幹事心的驅使下,我們還不悟,只想快點發完資料。我們四人分兩組。我們這組走不遠,同修就在平地上摔倒了。師父的一次次提醒,都沒有讓我們找出並去掉做事的人心,查找一下自己。在我們剛剛發了五、六份資料時,另一組同修告訴我們:快走,有人舉報派出所了。同修們此時都沒有了正念,在躲避的路上被警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異地看守所。
在看守所證實法
看守所共有三個女監號,我被關在第一個嚴管間,牢頭管的很嚴,不准和任何人說話,電視二十四小時不停播放亂七八糟的視頻,放的聲音很大。開始我正念不足,也跟著看,過幾天覺的不對,自己是煉功人怎麼看這些東西?便開始對著電視發正念,讓它沒聲音,過了幾天,電視真的沒聲音了。
看到別的監號有同修不穿馬夾,還能自由的煉靜功、背法。聽說同修為了開創這個環境,遭受了殘酷的迫害,一位三十來歲的同修被戴了一個多月的腳鐐。
我也想開創環境,便和幾位同修商量絕食抗議。到了那一天,同修有了怕心就沒做成。我就每天對著牢頭、獄警、看守所高密度發正念,心裏背法。我會背的法很少,原本會背的《論語》後面的兩段也想不起來了,但我會背哪句就背哪句,再利用放風、打飯排隊的機會,讓同修教我背法,反覆背。三個月的時間,我背會了《論語》。讓自己溶入法中,在師父的加持下,我一點點想起來二十年前會背的法,經文、《洪吟》等。
一天值夜班,我突然暈倒,小便失禁,醒來悟到還是要開創出煉功的環境。我就放下生死,不穿監獄馬夾,堂堂正正的在犯人坐板時煉靜功。獄警看到後也沒說甚麼。
我給牢頭講大法真相,但牢頭不接受,我就修好自己,善待周圍的人,用實際行動展現修煉人的善。我把自己的衣物送給沒有衣服的人,替不願意每晚輪流值夜崗的人值班到半夜十二點,有位年齡很大的犯人睡在窗邊,初春的夜晚是非常寒冷的,我看她很冷,主動和她調換位置,把我鋪的被子蓋在她身上,我就睡在光板上。牢頭看到大法弟子的善,對大法有了好的印象,主動聽我講真相了。
被迫害中堅定正念
四個月後,法院對我們四人非法庭審,在正義律師配合下,整個過程中我們就是講真相,他們都默默地聽著。第一次庭審就這樣結束了。第二次開庭也沒有被判處。第三次由於疫情在視頻上開庭,公檢法捏造假證據,我們四人分別被非法判刑兩年與兩年半。
由於疫情遲遲沒有下達判決書,我們仍然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我身上漸漸的長了常人所說的疥瘡,雙手、身體上都是,碰水鑽心地癢痛,奇癢無比。犯人們害怕傳染,非常的煩我,我沒了正念,用硫磺皂抹,卻越來越重。後來我悟到了,煉功人怎麼會長疥呢?怎麼能用人的辦法。我把它當成好事,發出強大的正念:不論是舊勢力迫害還是甚麼原因,我都不承認。我開始背法、發正念。
後來,原本的三個監舍合併成兩個,轉過來一個老同修,她的狀態也不太好,我與她切磋:目前疫情這麼嚴重,大淘汰已經開始了,我們還執著甚麼呀?我們要有正念啊!我倆靜下心背法,發正念,相互教對方不會背的法。隨著正念增強,我背法都背的頭腦空靈,身體發熱,三九天常人穿著厚毛衣還說冷,而我卻穿著薄的線衣褲都出汗,所謂疥瘡不知不覺的消失了。而那位老同修也找獄警說不「轉化」、不簽字。
我被劫持到監獄後,由於疫情需要隔離十五天,那裏規定每天上午所有人單腿跪著舉著右手報數,當時我就想到這不是拜邪靈嗎?但由於怕心也跟著做了。第一天腿痛,第二天腰痛,我悟到這是師父在點悟我,大法弟子是鏟除邪靈的,怎麼能拜它呢?第五天,我放下怕心,只蹲著,不舉手。包夾問我為甚麼不舉手,我沒有回答她,她就威脅要告訴包夾頭。看我不動心,也就不了了之。
半個月後,我被關入集訓監區二組。剛進去包夾就說:你不「轉化」你帶的所有東西都不給你。我沒有配合,只報數不舉手。她們開始罰我坐小塑料凳子,從早上四點開始坐到半夜十二點,一天只休息四小時,七天後我的臀部已經出血,血把棉褲都滲透了,但卻感覺不到痛,我知道是師父在為弟子承受!我白天背法發正念,腦子一刻也不閒著。電視播放和包夾念的「轉化」的東西根本帶動不了我,我也不回答她們的問話。她們看我不「轉化」,就整天羞辱、謾罵,大聲念「轉化」材料,有時候到大半夜,影響其他犯人休息,一個殺人犯就毒打我。這個監舍有十個同修,六個包夾,一個殺人犯,共關押十七人,只有我一人沒被「轉化」。包夾頭找三個已經「轉化」的,她們威脅我說:不轉化出了監獄就被送洗腦班,你能活著回家嗎?我根本就不相信她們的話,我有師父管,我只聽師父的,師父說了算。
包夾頭看軟的不行,在二零二一年臘月二十九那天,把監舍的窗戶都打開,揚言我不轉化就不關窗,讓大夥兒跟著挨凍。有四、五個人一起辱罵打我,拽著我的手強行讓我抄寫她們已經寫好的「三書」。我不寫差點把我的兩個拇指扭斷,我被迫違心的抄寫了「三書」。出去點名時我大哭起來。
半年後的一天,包夾頭叫我的名字,說:你去參加考試。她領著我就走,到那裏獄警給我一份卷子,我一看卷子是誣蔑大法的「轉化」卷子,我只寫了「集訓」兩字,立刻站起來對省「610」人員說:我不「轉化」!她說:你不「轉化」你來幹甚麼?趕緊回去!這給了我否定被迫違心抄寫「三書」的機會。
在被迫害的日子裏,我背法、發正念,在師尊的洪大慈悲與替弟子的承受下,走過了這個魔難。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對師尊的感恩,唯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以上是我修煉所在層次的心得,如有不對的地方,請慈悲指正!
(責任編輯: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