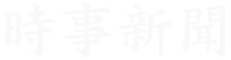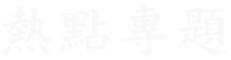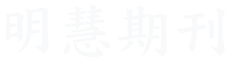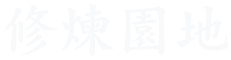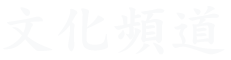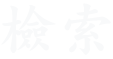十次綁架關押 四川女工程師控告元凶江澤民
董玉英女士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向最高檢察院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董玉英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實:
我從小體弱多病,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我重病纏身、身心都再也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偶然間碰到一個和我一道練過氣功的重病人,她整個人完全變了:年輕了,臉上白裏透紅,神采奕奕。我很吃驚,問她怎麼突然身體這麼好了?可找到了靈丹妙藥麼?她叫我馬上去煉法輪功。從此我走進大法修煉。
我修煉法輪功沒幾天,就開始拉血,拉了半個月,體重不但沒減輕,還重了。我知道師尊在給我清理身體,把我的病連根拔去。不出兩個月,我全身多年藥醫無效的疾病全部消失,臉上皺紋減少,白裏透紅。而我的暴躁脾氣也改很多。兒女們都很支持我修煉大法。
然而這麼好的功法卻遭到中共江澤民集團的殘酷迫害。從,從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的十六年中,我被中共人員綁架、關押十次:
第一次綁架:被非法拘留十天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帶了張真相資料,打算送到公安局,請國保大隊長董世紅順便轉交。董世紅和國保人員張兵立刻非法強行把我帶到公安局非法審訊一天,把我關到資陽城關派出所一間滿是屎尿、一米多寬,兩米長的黑屋子裏,然後非法拘留十天,拘留期間經常非法審訊我,並強迫我寫保證。
第二次綁架:被非法拘留十七天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早上五點,我到大眾鍛煉的地方東嶽山去煉功,被壞人舉報,被強行綁架,非法拘留十七天,關押地點資陽蓮花山拘留所。
第三次綁架:被囚派出所、拘留所、勞教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面對越來越殘酷的恐怖迫害步步升級,我走上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高呼「法輪大法好!」「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被天安門廣場便衣警察綁架。在駐京辦非法關了幾天後,我被雁江區國保大隊警察黃光武等銬上手銬帶回資陽,關在城西派出所滿是屎尿的小黑留置室四十八小時,又非法關進蓮花山拘留所。期間,雁江區「六一零」曾辦洗腦班,強迫聽誹謗、看誣陷法輪功的書。不久,雁江區公安分局及「六一零」非法批我一年半勞教。我堅決不承認這種迫害,未簽任何字。在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因體檢不合格未收,又把我重新關進拘留所。二零零一年三月中旬,我心臟停止跳動大概半小時,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出獄。
第四次:被關戒毒所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四點,我在親戚家被警察綁架。大邑刑警大隊長周文才帶著七、八個警察,提著手槍,拿著手銬、繩索闖進民宅,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強行抄家,抄走很多法輪功資料。警察用槍口對著我姪兒的太陽穴,然後五花大綁捆上;七十歲的親戚也被警察銬上手銬綁架走。周文才狠狠打我、踢我、搧我耳光,把我打得眼前金星直冒。然後用手銬把我兩臂一上一下背銬在後,幾分鐘就痛得我臉通紅,汗水直冒。周文才等警察把我們劫持到大邑刑警大隊,分別暴力取證,我再一次遭警察毒打、背銬,三十六個小時不准解便、睡覺。一警察還故意把手銬用力往上提,我聽見喀嚓聲,我肩膀關節被提傷脫臼,痛得我不由自主喊了一聲。我肩膀痛了半年多。
同修廖大姐絕食抗議,我立刻絕食聲援。第十天,戒毒所所長張某把我「大」字銬在鐵柵上強行灌食,他親自動手,抓住我的頭髮,一把把我的頭扯進小於我頭部的兩鐵柱子中間,當時我就失去知覺。後來頭部兩側腫起老高。由於殘酷迫害,十月三日晚,我突然心臟病發作,休克五個多小時。與此同時,同修廖大姐被酷刑折磨致死。大邑與資陽雁江區公安分局怕我死去擔責任,暫放我回家。為避免他們持續迫害,我離開了家。第三天他們就來抓我。為抓住我這個老太婆,他們出動了一百多個警力。
第五次:遭非法勞教一年半監外執行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乘車到雁江區石嶺鎮發放真相資料,遭人惡告,被石嶺派出所警察綁架。關了一個月後,把我拉到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獄醫一聽我心臟立刻不收,又照了心電圖,更不收了。石嶺派出所警察朱小勇與楠木寺勞教所獄警大吵,強迫他們收下我,說勞教所醫療條件好。獄警大隊長罵朱小勇:「比我們的心還黑,死都弄到我們這裏來死!」堅決不收。朱小勇、周付昌只好將我拉回,又關了我十天。過了很久,送了一張非法勞教一年半監外執行的通知書給我。
第六次:被非法關押一個月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我到米易一朋友家,剛坐下幾分鐘便被米易丙谷派出所警察綁架,逼供一天一夜,說我是外地人,去米易走親朋家是非法串聯,將我非法關押一個月。
第七次:被非法關押一個月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日,幾個善良常人把我從便衣警察嚴密包圍、監視中救出去,把我帶到大邑安仁鎮鄉下去修養。誰知我們還未進院子,門口兩個老太婆叫我們快跑,說房主幾天前被抓了。我們趕快離開,剛走了幾十米,就被追上來的警察綁架,當時我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覺。安仁派出所警察把我和小王銬上手銬,通宵刑訊逼供,我的臉上、腿上都被打傷、踢傷。從六月二日下午到六月六日下午,整整銬了我四天四夜,不許我睡覺。晚上警察們睡覺,便把我吊銬在窗戶上。除了兩個警察外,其餘的都不許我解便。
姓徐的大胖子所長不停的破口大罵,「你是政治犯,對你們政治犯沒有法律可講。弄死你,我們還得獎呢,弄死你敢做啥?」他們不停體罰我。姓楊的所長對姓徐的所長說:「把她弄死算了,弄死了就上報說她自殺了。」六月五日下午,我突然心臟不舒服,全身抽搐,警察無動於衷,還譏笑、辱罵我。六月六日,朱小勇一見我便罵:「你怎麼不死了?死在哪個溝溝裏多好,死了當爛你媽根粑紅苕。」
六月六日下午,朱小勇、黃光武再一次把我綁架進雁江區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口頭、書面用憲法、刑法,揭露他們執法枉法,殘酷迫害我的事實。一個月後,我被取保候審。
第八次:被囚看守所、洗腦班 遭藥物迫害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我乘284次特快列車從成都到上海。十四日,我給一個病人推薦「常念法輪大法好可祛病」,被一個男便衣特務、一個女列車員竊聽後綁架,非法關押遭資陽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我被四川省資陽市、區政法委、「六一零」、國安、國保由資陽看守所秘密綁架到新津洗腦班──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在新津洗腦班,我遭到了巨大的羞辱和摧殘,給我原本和諧正常的家庭、社會關係帶來破壞。他們用暴力強迫從我血管裏輸進破壞中樞神經的毒藥。這種藥一輸進去,我立刻嚴重幻視幻聽、精神嚴重躁狂、緊張、恐懼,心胃處劇烈難受,每一個腦細胞都在被嚴重殺傷當中,每分每秒都在拼命,都要用盡全部意志,才能控制精神不突然分裂。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吃中飯時,看見吃剩的飯菜湯裏有白色粉狀物。我的飯由「陪教」打,湯飯菜和在一起。我馬上問:「誰在我飯裏下了藥?」三個「陪教」破口大罵,叫來洗腦班骨幹殷得財,殷得財甚麼也沒說,看了一眼就走了。半個多小時後,藥性發作:頭昏沉、嚴重嗜睡、心胃不舒服、煩躁緊張。徐丹來抱走被子、體罰、不許睡覺。逐漸的,我全身生理機能失常,各種疾病紛至沓來。而這一切都是洗腦班主任李峰精心策劃、殷得財實施、指使、教唆的。用李峰的話說,他是「牽口袋」的人。
幾天後,在第一步不停實施的基礎上,他們開始了第二步。殷得財把我叫去一邊高聲叫罵、威脅,一邊編造說我寫了甚麼東西等等。殷得財是直接指揮、安排並實施迫害我的最邪惡之徒。他一天要數次到每個監房看法輪功學員的狀態,以便針對狀態迫害。他高聲恐嚇、叫罵、羞辱、指使打手與他一道用各種非人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他多次在我面前表白,說他本質不壞,可是這個「本質不壞」的人卻是最凶殘、最賣力迫害正信、迫害善良的邪惡。成百上千的大法徒的正信被他惡毒的迫害,成百成千的大法徒,被他直接並指使他人用盡各種方式瘋狂的羞辱、折磨。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折磨致瘋,而這個人卻是律師!他說他是中央派下來的,是經過中共中央「六一零」培訓的,甚麼特務伎倆和流氓手段他全部具備。凶殘的邪惡小人徐丹,就是他調教的得力打手。
我的身體狀況在毒藥作用下越來越差,接著,幾個彪形大漢把我拖上車到醫院「看病」,然後一個約三十歲姓周的花橋鎮醫院醫生,第二天拿來幾袋配好的黑色液體藥,在洗腦班裏強迫我輸液。(洗腦班裏輸液架等一應器具齊全)我雖然堅決不輸液,也決想不到他們會給我輸破壞中樞神經的毒藥!輸進去沒多久,突然眼前變得模糊,開始出現各種幻覺、耳中出現各種聲音,頭劇烈難受,一種所有腦細胞被嚴重殺傷的感覺,分分秒秒都在拼命掙扎,要用盡全部的意志強力控制,才能使精神不突然分裂。心胃處劇烈難受,嚴重躁狂、恐懼、緊張。我要求姓周的把那些黑色液體的藥名和使用說明書給我看,姓周的沒拿出來。後來毒性反應越來越強,到第三天我拼命不許他們輸。姓周的還不甘心,罵罵咧咧的說藥很貴就浪費了。這種毒藥的毒性一直持續到兩年後的今天還時有發作。如果我不是拼盡全力控制、不停在心裏念頌「法輪大法好」,可能像祝霞一樣瘋了,也可能像劉生樂、李曉文已經死了。連殷得財都當我面說我目光呆滯、行為呆傻。他們把我送到上海家人處時,我的家人都說我變得不認識了,並且記憶也喪失大半,頭髮也幾乎全白了。
在這種危險情況下,高小牧趁機死逼我寫甚麼「深入揭批」。五月一日,高小牧說她向省裏要求加班給我「洗腦」,每天加班費一百二十元錢。不管她怎麼強逼叫罵,我堅決拒絕。
第九次:被洗腦班迫害半年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早上,我在家開門丟垃圾,幾個惡人從我對門的資溪司法所辦公室內衝出來,把住我家門,將我強行綁架後抄家,搶走私人財產:所有大法經書、資料、光盤、電腦等,並把我綁架到二娥湖洗腦班迫害半年。
第十次:被非法判刑 遭上海女監殘酷迫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晚,嘉定區南翔鎮派出所十幾個警察湧進我借租房內實施綁架、抄家,抄走大法經書、光碟、資料、優盤、兩台電腦。被嘉定區法院枉法誣判三年六個月徒刑。
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綁架到上海市女子監獄。一進監獄,監區長仇敏穎即已安排了「轉化」我的監房環境,遭到我的堅決抵制,後一直被嚴管迫害。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中隊長黃豔裔毫無理由的把我關進禁閉室,叫包夾犯朱玉燕把收錄機音量開到最大,置於我身邊,正對著我滾動播放紅歌,從早到晚十幾小時的用高音強烈刺激,不顧我血壓210/140高壓,不顧監獄衛生所醫生招呼;打電話到監獄炊廠叫虐待我,每頓只給平均量三分之一量的菜,時間長了之後,導致我嚴重缺鉀、維生素而陣發性昏暈;唆使朱玉燕、王潔平在倒著拖我到禁閉間的路上,把我高高提起,然後突然放手,把我仰面摔在地上,我頓時昏迷過去,很久才甦醒。黃看我醒過來,立刻打開紅歌高音喇叭刺激我。她知道我血壓高,故意摔倒我,其用心可想而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無任何藉口的把我關進禁閉間。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十二日,獄警朱世惠以「抄《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範》時,沒有抄「邪教」兩個字」,第三次把我關進禁閉間,並對我上約束帶一週多,一天二十四小時,睡覺、吃飯、解便都不解開。
二零一五年五月,上海監獄局對監獄下達對法輪功學員必須達到百分之百轉化率的邪惡命令,上海女子監獄六月專門組成「攻堅組」,由副監獄長李翠萍負責,由迫害法輪功的專管監區五監區(現三監區)監區長仇敏穎直接組織、具體實施迫害。獄警茅穎說:「十多年都沒見過這麼大的陣仗。」
二零一五年七月初,獄警劉碧雲專門向我宣布監獄決定:「監獄決定用擠壓的方式轉化你,叫你生不如死,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要你繼續堅持你的東西,就人不知鬼不覺的幹掉你!」
從二零一五年六月開始到二零一六年二月底,我被仇敏穎指使六個包夾犯滅絕人性的折磨,遍體鱗傷,內衣血漬斑斑,每天的舊傷上都會增添新傷,滿頭、後頸、兩腋下、雙乳房、雙膝、雙腳、雙手的烏青紅腫從未消失過,至今雙腿雙臂傷殘未癒,韌帶嚴重受傷,行走困難,上下樓梯疼痛難忍,左手不能彎到後背,右邊腰部被打傷處至今坐一會兒就劇痛。
在長達八個多月,二百多天的日日夜夜,從早到晚,從晚到早,我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於被迫害中:每天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十點或十二點,長達十七個小時以上的體罰、打罵,然後抄寫白天罰抄的東西,抄二、三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睡下之後剛睡著便被包夾犯打醒、踢醒,每天如此,每晚如此。特別是在行刑房的日日夜夜的酷刑折磨,多次被毒打昏迷過去。
仇敏穎多次恐嚇我:你出去敢暴露這裏的監管秘密,你就等著麻煩,等著再次進監獄!劉碧雲也說:你出去守不好口,敢多話,有你的麻煩。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6/12/27/1604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