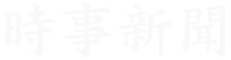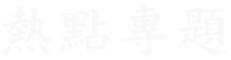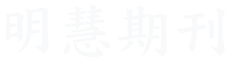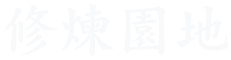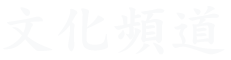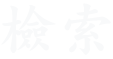廣東高州劉惠榮自述遭受的迫害
自從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以來,劉惠榮和家人就過著擔驚受怕的生活。劉惠榮自己曾經被迫害十幾次,家人也受到恐嚇和株連。其二姐因為她不「轉化」而不能升職。中共邪黨還恐嚇其兩個妹妹,如果劉惠榮不「轉化」她們的兒女就不能上大學或不能當兵等。
下面是劉惠榮自述被迫害的經過。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法輪功後,我經常被無故非法關押。當時身體還不是很好,走路困難,全身浮腫,雖然是好轉了,但還未康復。
高州河西派出所比其它派出所邪惡,只要他們上級有活動,就先把我們法輪功學員綁架關押,時間不等。比如江澤民來高州,我和本村的幾個法輪功學員都被河西派出所的警察提前綁架,非法關押在招待所一間房間裏,不給飯吃,天天是妹妹送飯,一群保安守著,直到江澤民離開高州才放人,共七天。李長春路過高州時我們又被非法關押幾天。
有一次在家門前見到一姓譚的學員夫婦散步路過,人之常情,請他倆到家裏坐,一杯水還沒有喝,我和姓譚的學員夫婦就被河西派出所的警察綁架,並分開「審訊」,關押二十四小時放回家,搞得人心惶惶。因為我家門前屋後都有便衣和保安蹲坑。
「七二零」後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繼續在公園煉功,被高州警察抓走,當時有學員被警察打,我們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戒毒所十五天,十五天內勒索家人給一百二十五元飯錢。
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家人整天提心吊膽,擔驚受怕。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天天到我家來騷擾,所長張嘉義帶隊,一群警察有時早上天還沒有亮就來了,有時上午、有時中午、有時下午、有時半夜,時間不等,還安排一個叫鐘克志的保安專門到我家來「上班」。天天早上七點半就到,嚇得我家妹妹的小孩哭。我叫他到外面去,使我家人抱怨我。
那時我的心很沉重,也很無奈,不知怎樣好,當我得知很多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要講清法輪功真相時很感動,自己也決定去上訪。
一天早上,我很早就背著行李向北京出發了。因天亮警察會來我家的。一路上想著到北京後怎樣跟上級領導講清法輪功真相。在北京西站下火車我就上了一輛公巴,先到天安門,在廣場上看見很多警車呼叫。有警察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馬上背後就被打了一掌,並抓上車拉去一個地下集中營,抄了我身上帶的錢,將我和其她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一起關押。在那裏呆了三天,茂名一科的警察將我押回轉給高州河西派出所,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將我先關押在一個黑黑的屋裏,第二天嚴刑「審訊」。之後將我送到戒毒所拘留十五天,出來前也是要家人給了一百二十五元飯錢,紙巾錢另計。戒毒所裏給我們的飯很難吃,菜基本上是吃黃豆。
經常被抄家,家人被嚇得不像樣,還要面對不明真相的人說三道四,指指點點,心理壓力很大,精神受到嚴重傷害,我理解家人的痛苦,但家人不理解,說我自私,要我放棄。
有一次我出去買一些日用品,去的時間長一些,回來家又被抄了。看見家人害怕痛苦的樣子,我心裏很難過。這次河西派出所警察在我家抄家時,在縫紉機肚裏找到一張經文,同時也抄其他法輪功學員的家,家裏有大法資料的法輪功學員全被非法勞教二年。上午非法抄家時沒有抓到我,下午又來。我在家反鎖不開門,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和「六一零」、國保、街道辦的人就留下守著我家門口,有的回派出所拿工具、梯子來,準備砸門和上樓頂綁架我。我在他們回去拿工具時從樓頂走掉了,回頭看我家樓頂有很多警察。
我在家不能呆了,就再次上京上訪。在火車上遇見很多法輪功學員,當火車在河唇停車時,我們就轉到其它的車去,到淶水檢查身份證時我們被扣押在淶水派出所。警察得知我們是法輪功學員,就非法搜身,抄走身上的錢。我們在那裏被關了一晚,被通知的茂名駐京辦事處的人來接。我們要求給回我們的錢,自己買車票回家,警察不同意,我們就不願跟他們走,結果被毒打。「審訊」時也打過。茂名駐京辦的人強行把我們拉上車,送往茂名駐京辦事處四樓關押。在房裏我們十三人就反鎖,要求還給我們的錢自己回家,明知他們不會善待我們的。
在窗口我們打橫幅,叫「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背著《洪吟》〈無存〉。到凌晨天還沒亮,他們就開始砸門,外面叫來消防車升起雲梯,也掛起氣墊,氣墊是沒有打結紮穩的。我們看見有氣墊就想跳下去找機會跑,不能落在他們手上,結果就出現了北京跳樓事件(明慧已經報導)。
因為氣墊的繩子沒有打結,我們跳下去摔得不同程度的傷,有骨折的、有斷腰椎骨的,還有一個當場死亡。我當時不省人事,醒後腦震盪,頭暈的不能站,左手抬不起,肋骨痛得要命。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二天警察把我們押回高州,在火車上警察把我們兩個一對的銬著,睡、坐都困難。回高州後將我們分開在各個派出所「審訊」,我在河西派出所幾天幾夜不給睡覺,警察輪班看守「嚴審」,不知過了幾天將我關在黑房裏,在黑房裏又呆了幾天就送去高州市第二看守所關押。在看守所裏我們都有傷,忍著痛天天做奴工燈飾,不完成任務不給睡,沒地方夠睡我和幾個法輪功學員就睡在地上。
二零零零年除夕前,警察把我們法輪功學員用車拉到觀山招待所,領來一幫從三水勞教所來的所謂「幫教」人員,想「轉化」我們。當時有幾個「轉化」的當晚就回家了,沒有「轉化」的後來轉去高州市第一看守所,並非法判刑,三到七年不等,我被非法判刑三年。
我在非法關押期間身體狀況惡化,不能煉功腎病嚴重,全身水腫,不能吃東西,走路困難,還要天天做燈飾,要求任務減半都不同意。後來就被迫害到大、小便拉水,身體又變成皮包骨,不能走路,連四肢都不會動,像個活死人。拉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生命危險,各個項目指標都不正常,很嚴重了,活不了幾天了。在醫院打點滴,我一打點滴身體就抽筋,呼吸就困難。回到看守所的甚麼事情都要找其他被關的法輪功學員幫忙,學員要求警察放人,不然我會死在裏面的。這種情況下,高州市各級官員到看守所來看我,看見情況屬實,還要我寫保證書才可以搞保外就醫。我不同意寫,怎知他們叫我親人寫了。
我回家後身體很差,妹妹不放心將我接到二妹家送廣州南方醫院治療。「六一零」和國保人員要了我妹妹家的電話聯繫跟蹤。有天打電話叫我在某日某時必須回高州市第一看守所報到。我回家按時到一所報到,怎知他們是叫我回來開宣判大會的,當著各中、小學的學生,還有群眾的面宣判我們刑期,開完會後我們就被用車拉去遊街示眾侮辱。
二零零八年,我和法輪功學員去高州謝雞鎮義山村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謝雞鎮派出所的警察綁架我們轉給高州「六一零」。他們拘留了我們十五天後又送茂名洗腦班迫害,直到開完奧運會才放回家,有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四月份,高州「六一零」夥同國保、寶光街道辦的人來我家綁架我去洗腦班迫害。我在裏面煉功,被他們幾個人衝入房間將我從床上拖下按在地上,雙手向裏反扭,向上抬,痛得我直叫。張衝雲猶大在場不加阻攔,還在一旁幸災樂禍。我雙手被扭得抻不直,又腫又黑,雙手手掌心和指尖出水向外滴。第二天他們假惺惺的問我要不要藥水。我不理照常煉功,三個月後雙手伸直才不痛,六個月回家。
二零一一年我又被綁架去洗腦班迫害,強制寫了保證書一個月後放我回家。在這裏我希望那些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早日清醒,不要做歷史罪人,希望世人早日明白真相,停止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