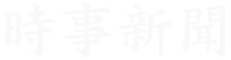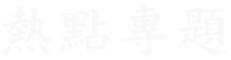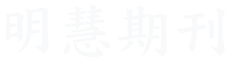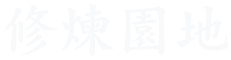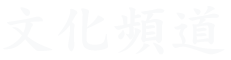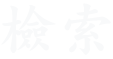在黑窩走正修煉路 證實大法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末,我幸運遇到《轉法輪》寶書,從此走上了返本歸真之路,師尊無條件的給我淨化了身體,使我無病一身輕,二十年沒吃過一粒藥。丈夫看我身體好的這麼快,簡直不可思議,他也跟著我一起走入大法中修煉了。
修煉大法使我變的神清氣爽,一家四口人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真是其樂融融。家裏沒有了病人,掙的錢也就夠花了。那時七、八歲的一雙兒女有時也跟我們坐在炕上圍一圈盤腿打坐,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真是幸福快樂。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跟妹妹、丈夫同修走上了天安門證實大法。十一月一日,我們被遣返回當地看守所迫害十五天。在放我們回家前,他們還強行向我母親勒索錢財,連伙食費帶罰款共計一萬多元錢。我從看守所回來不久,又被居委會長舉報,次日把我從家中強行綁架到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一個月。
由於當地邪惡無理的干擾我們的正常生活修煉,所以我們商量著要二次進京上訪,要求還大法師父清白,給我們一個沒有干擾的修煉環境,堅持真、善、忍的信仰沒有錯。於是,我於二零零零年三月邪黨「兩會」期間,第二次進京上訪,在天安門被抓,遣返當地後,被非法勞教二年。
廣傳真相救度眾生
二零零二年十月,當地傳送資料的同修被迫害,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正念》那篇經文發表,外地同修冒雪來我地,把經文送到我手中,我主動承擔起本地區傳遞資料項目,那個時候,資料供不上時,我和倆孩子就用手抄寫簡單的大法真相,往眾生家門口放,倆孩子還用紅紙摺了很多千紙鶴,在兩個翅膀上寫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賜幸福平安」等,大面積的往眾生家送,還很好看。我們當地的同修那時候也不知道累,也不知道怕,商量好搭個伴,黑天就騎上自行車,去周邊農村發資料去,那時農村路還都是土道,高低不平的,周邊幾十里都發到了。
在當地,我帶著十二、三歲的兒子(小同修)走遍大街小巷發真相,很晚才回來,第二天干啥都照常不誤。零三年、零四年兩年,我負責傳遞真相資料,那兩年,我風雨不誤,同修一個電話就趕過去,從未耽誤過。為了躲避邪惡,出去或回來,我背著兜子都要走很遠的路,真感到師父一路看護我。零三年冬天,資料少,出去一趟就取一點資料,我就和鄰地取資料的同修商量,去×市同修那多拿些真相資料來,那離我們這八百多里路,從那我們帶回來大量的真相資料,回來的路上,也遇到了有驚無險的事情,都在師父的保護下躲過了。這裏就不詳細的敘述了。
我們這週邊沒有資料點,資料缺乏。零四年冬天,為了救度眾生,我去某市同修那裏學習打印、電腦、上網下載等技術。我是小學文化,我看著那些東西都發愁,咋學呀?同修都鼓勵我說:「好學,修煉人一切都是超常的。」同修們耐心的教我,一步一步給我寫在本子上,我一步一步的學,甚麼都是同修給的,我只是在家幹活,配合當地同修發資料。
零四年《九評》剛發表,我開始大量做《九評》,當時《九評》需要量大,我一夜夜的打印,放鬆了學法修心,當時丈夫同修家親戚對我干擾大,丈夫的兄弟、姐妹們要把他們癱瘓的父親送到我家伺候,他們的後媽看他爸癱瘓了,就走了。他們家人都很勢利,在我的一生中,跟我沒有任何往來,這時我對他家的積怨一股腦的湧出來了,沒有理性的處理好家庭的問題。
後來當地同修去外地發《九評》被非法抓捕了,承受不住迫害,說出了資料是從我這來的。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家資料點被破壞,實質上是我修煉沒跟上,自己沒修好,被邪惡鑽了空子,給我的家庭及當地救度眾生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零六年我被投入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迫害五年。
最艱難的歲月
1.酷刑迫害 喚醒倆昔日學員
黑龍江省女子監獄是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惡的黑窩之一。零六年、零七年時,上面下密令強制轉化堅定的大法弟子,要求百分之百轉化,他們喊出「不轉化就火化」的口號。我被從新從教室調到了九監區五樓,那裏是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大約七、八個房間,門全用白紙粘著,眼睛高處只留一手指寬的縫,以便警察從那縫處窺視大法弟子。
那裏陰森恐怖,一個屋裏關押一個堅定的大法弟子,一幫迫害大法弟子的犯人,有一至兩個邪悟的。我被關在牢頭那裏,每當聽到開監欄門的鐵鏈子響時,再加上警察走路的皮鞋聲,更顯得陰森。我被強制坐小凳,從早上坐到半夜,一個邪悟的和幾個職務犯人每天對我所謂的幫教。一開始給拿一些好吃的,被我撥拉一邊,晚上不讓我上床睡覺,一幫犯人硬把我按在小凳子上,他們嘴裏嚷嚷著「不轉化」還想睡覺?每天就這樣折磨我。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監獄有駐監檢察院、檢舉箱,在押犯人有寫檢舉信的權利,我就跟犯人頭子說:我要紙和筆,我要寫檢舉信,她問我要檢舉誰?我說要檢舉陶大隊長,她迫害我。犯人頭子報告了陶,陶說:行啊,但是只給我半小時時間,而寫完了不讓我親自往信箱裏投,得交給她。我說:行。我只有小學文化,給我半小時寫檢舉信,當時氣氛緊張,犯人頭看看表:寫吧,半個小時。
我把給我的紙往桌子上一鋪,手握起筆,心裏求師父幫我寫檢舉信,然後我就刷刷的寫完了。記不清原文了,大致有以下內容(並給陶姓隊長附上一封信):一個個貪官污吏有甚麼資格對修煉真、善、忍的大法徒進行所謂的「幫教」,她們才是真正的罪人,請給她們找真正贖罪的地方,不要讓她們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請陶立即停止犯人迫害我,我有出去那天,否則,我將在國際法庭上控告你。
我去陶的辦公室親手把信交到她手裏,她一臉滿不在乎的樣子,實際對她起到了很大的震懾,在以後的日子裏大大的收斂了對我的迫害。
有一次,監獄體罰大法弟子站在地磚上,從早上起床站到後半夜兩點,就讓那麼站著,有站暈過去的;有站倒下的;還有不少受不住這種體罰「轉化」的。讓我臉朝牆站著,我不站,犯人把小凳往一邊一踢,一幫犯人把我抓起來,先用寬膠帶粘住我的嘴,從脖子後往嘴上一圈一圈的繞,勒得我上不來氣,又把我的雙手從後面反捆上,然後把我整個人抓起來腳離地,就那麼貼牆上,犯人們怒吼著:不站就給你貼牆上。就那麼迫害了我兩個多小時。這期間,又有警察進屋,把臉扭一邊,裝作看不著。
一看我實在不站,又罰我坐小凳,坐到半夜。有一天坐到半夜兩點多,一幫犯人把我推到牆角,陰森森的恐嚇我,再不「轉化」就整死你,這深更半夜的整死個人誰也不知道,在那裏有同修被迫害死、致殘、致瘋的……我的精神及肉體也已承受到了極限。我告訴自己,不能崩潰,從構成我生命的本源上發出強大的正念:邪惡你妄想。我求師父保護,救我出去,我一定出去,我要走完修煉的全過程,跟師父走。
正邪的較量中,我放下人心,放下生死,放下世間一切,發正念,背法,背呀背……
邪惡仍不死心,又找兩個邪悟的人來「轉化」我,這時師父的法:「我的根都紮在宇宙上」[1],出現在腦海,頓感自己變的高大,正念覆蓋那個場。有一天,犯人頭上我跟前,用她的肩膀靠靠我的肩膀:「媽呀,你啥時轉化呀?折磨死我了。」每次她們迫害完我,她們都表現出身體難受的樣子,她們跟我說話也變的客氣了。
我跟犯人頭說:你知道我以前從不跟邪悟的人談話,今天,你讓我跟她倆談話,我有一個要求,得讓我背法給她倆聽,我背完法,我們在法上切磋,看看誰的理能在宇宙中立足,就聽誰的。
那個犯人頭樂了,行。只要你張口說話就行,背啥都行。我說:我要是把她倆正過來,你就跟我煉法輪功。她說:行。但是累死你(那意思不可能把她倆拉我這邊)。我看著眼前昔日的同修,心裏求師父幫我把她倆拽回到大法中來吧。我對她倆說:你倆先聽我背法給你倆聽,好嗎?等我背完法,咱們在法中切磋,好嗎?她倆說:行。我大聲給她倆背法:《論語》、《洪吟》、《洪吟二》、五十多篇經文、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會講法》、二零零七年《美國首都法會講法》、二零零六年洛杉磯法會結束前師父那段講法。背了一天,從早晨吃完飯背,一直背到晚上開飯前,我在這背,有幾個犯人一邊聽,有個牢頭一看我大聲給她倆背法,就問犯人頭,說我這是幹啥呢?犯人頭說:別管她,讓她背。
「法能破一切執著,法能破一切邪惡,法能破除一切謊言,法能堅定正念」[2]。法的威力清除了干擾她們的因素,她倆知道錯了。我又給她倆背《建議》,她倆說錯了,我說:寫「嚴正聲明」直接交給陶隊,寫完了先放好,陶她們得讓你倆跟我談幾天。飯來了,我們三人圍在一起,她倆拿出好吃的與我共同分享。
「修在自己,功在師父」[1]。在那最邪惡、最殘酷的環境裏,師尊給弟子開創了公開集體學法的環境。有一天,我們三個正在一起做吃的(拌個菜),陶來了,說看看我們談的咋樣了?犯人頭說:挺好的,你看看某某(指我)從來誰都不搭理,現在她們三個在一起吃飯呢。陶樂了。我看她轉身出去時樂的小辮兒直撅的(她腦後紮個馬尾辮)。
那是一週的時間,我們在一起發正念,沒人的時候,我就給她倆背法,有人時我們就嘮別的。後幾天時,犯人頭覺的不對勁,一直沒聽著她倆說邪悟的理論,用巡視的眼光看我們了。週一的時候,陶上班了,讓她倆去辦公室彙報跟我談話的情況,她倆把早寫好的「嚴正聲明」拿著到辦公室,就交給了陶。辦公室和監視室只隔個柵欄門,就聽陶對那兩個同修連喊帶叫:怎麼會這樣?我在監室裏發正念。
不一會,犯人頭回來了,叫我收拾東西,直接把我又送到新入監犯人教室去了。沒多久,把我送到二監區,剛到二監區沒幾天,女監六一零頭子去了,那裏警察問:毛主任,你幹啥來了?六一零頭說:沒事,我看看哪個是某某某。監室的門是開著的,警察領著六一零頭在走廊一走一過,就看著我了。那時我穿著一身褶巴的破囚衣,我被迫害的很瘦,穿一雙老頭大棉鞋,我一米五三的小個子,往那一坐,一小堆兒,實在太普通了,只有我心裏有師父、有大法,是強大的。
2.在二監區邪惡的黑窩裏
二監區,那裏是關押重刑犯人的監區,一半兒以上是殺人犯,每個監室都有大法弟子被非法關押迫害。剛到那裏,每個監室的門都掛著白布擋著,不讓每屋的大法弟子見面,每個大法弟子跟前都有兩個所謂包夾犯人,大多數是殺人犯,寸步不離的看著大法弟子。
那裏有五個同修,我們終於聯繫上,共同反迫害,開創環境。到洗漱時間,拿臉盆一起去水房,把門上掛的白布拽掉,犯人不讓,拼命的擠住門,那個門,大法弟子往外推,一幫犯人往裏擠,連拉帶拽,幾天下來,門就拽壞了,折頁拽掉了,也關不上門了,有的門把手也拽壞了,有一天董岩(迫害大法弟子的隊長)遛道,看到門那樣就問:這門怎麼這麼耷拉著?知道的犯人說:都是她們幹的。
惡人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不公正的,我找隊長談話,講真相,講大法在國際洪傳,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歡迎,正法必成,大法弟子是遵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沒觸犯國家任何法紀法規,我是合法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權利,這也是我在遵紀守法,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是江澤民犯法。大法弟子沒犯法,我沒有犯法,我們被非法關押在你這裏,請您明智,不要操縱犯人迫害大法弟子,我們是大法弟子,學法煉功是天經地義的。隊長說如何如何不行,在這裏的犯人得如何遵守監獄監規。
我說: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我不是犯人。對我們的迫害是共產黨強加的,我是不承認的,連續大約三個月,我們五位同修每天早晨煉功,犯人迫害我們,那段時日,每天都像打群架似的,大法弟子往那一站,或一盤腿,犯人像瘋了似的把大法弟子撲倒,同修們就開開窗戶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那段時間監獄上空,「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此起彼伏,洪貫穹宇。
由於大法的加持,加上同修們共同發正念,真切感受到操控壞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生命清除了。我們幾個同修身體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都去找隊長正告他,我給隊長寫信: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罪,他們承擔不起,不要再執法犯法。再操控犯人迫害我們,就向有關部門控告你。看我們身體被犯人迫害的,我們幾個同修都經歷了多年非法關押迫害,體質都很弱,如果再讓犯人迫害我們,誰有生命危險你全權負責。咱們同是炎黃子孫,生命在輪迴中也許哪一世,我們曾經血脈相連,血濃於水!不要相信江澤民的一面之詞,對法輪功的打壓,對我們這些大法弟子的殘酷迫害,正如「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來順受」[3]。師父的經文時常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於是我寫了一篇《鄭重聲明》大致如下:尊敬的監獄領導及二監區的大隊長,我們幾位大法弟子因堅持對真善忍法輪大法的信仰,不幸被非法關押在這裏被迫害,請大隊長及監獄長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立即無條件釋放我們。我們不是犯人,不服從中共邪黨的任何命令、安排、指使。我們期待你們的消息。大法弟子某某某,其他四位同修一一簽上姓名,交給隊長,隊長交給了監獄長。
我們脫掉了囚衣。我們學法、煉功、發正念,向迫害我們的警察犯人講清真相,打人犯法,執法者打人罪加一等。你們都知道法輪大法,在你們的權利範圍內,善待這裏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將功德無量。我不穿囚衣,監獄不讓我們見家人,在二監區三年沒出過監室牢籠。
背法帶我走出紅塵
環境開創出來了,邪惡用親情動搖修煉,多年見不到家人,對兒女的無限牽掛,我在心裏默默求師父幫弟子從紅塵中拔出來,面對牢籠鐵窗,難耐的寂寞,我背《轉法輪》,把法溶在生命的微觀中,壓入構成我生命的本源深處同化法,我好好珍惜,珍惜師尊對弟子的看護,一步步從殘酷迫害中走出來,從生死存亡中一次次把我救起,寫到此處,我已淚如雨下。
在二監區遭受三年迫害的日子裏,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背下了《轉法輪》寶書。然後就二天背一遍《轉法輪》,師父的很多講法,我抄了大約三分之一。越抄法、背法,越感到法的可貴,我為自己的生命慶幸,幸遇師尊救度!
學法、煉功、發正念、抄法時間過得飛快。
不穿囚服的這三年,犯人給我的一件粉色棉布立領襯衣領根處已補了十一處核桃大小的各色補丁,衣袖衣邊全磨飛了,冬天穿的棉馬甲裏子全磨沒了,全露著棉花直到穿回家。
同監室的犯人說:姐,你穿的衣服帶回去吧,將來你們平反了,你穿的衣服送到博物館去。同監室的比我大十多歲的也管我叫姐,她們說,我好像是她們的家長。看我的犯人有時說話跟我大聲喊,我不吱聲,別人就說她,跟咱某姐說話客氣點。
我走出監獄的時候,她們都哭了,好幾個人把頭蒙在被裏哭,我囑咐她們一定要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跪拜謝師父!
在證實法反迫害救度眾生這一路走來,處處與各方面的人正面接觸。初期的時候,公安系統的人,大多不明白真相,有人罵我瘋,有人罵我傻,嘲諷我,用世俗的眼光看著我。師父講:「至於說社會上怎麼看我,我想我與大法只要走的正,我的學員只要做的好,不管有多少偏見,我想都會扭轉過來。(鼓掌)所有對我們不理解的人、攻擊我們的人,都講著同樣的一句話:你們做的那麼好?不可能。就是說他不相信人類還能有好人存在,那麼我們就做給他們看一看!!!」[4]師父的這段法牢牢的記在我心裏,在我遭受冤獄迫害的歲月裏,有多少人圍著挑不是,挑不來,時時處處用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心懷真善忍 修己利與民」[5]。晚上睡覺前,找自己這一天哪句話說錯,哪件事做的不夠符合法,認識到了及時歸正。
在看守所裏遇見一個犯人要自殺,我耐心的勸慰她不能自殺,自殺是有罪的,怕吃苦自殺是逃不了的,只能給自己造成更大的痛苦。教她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生病了,吐的哪都是,我幫她擦洗乾淨,坐在地上靠著床邊看著她,她睡著了,我也睡著了。看守所長看到了很感動,說謝謝我。我到哪,就把大法弟子的純正美好帶到哪。
在哈監九監區、新收教室那段日子裏,每天都接觸從全省各地看守所送去的犯人,剛到室的犯人都很恐怖害怕,而且帶去的物品、被、褥零亂,需要整理,我就藉這個機會主動接觸她們,幫她們縫做被褥、褥單,這樣給她們講真相,勸三退都接受。監獄對新入監的犯人管的很嚴,喝水都不能隨便去打,不敢去,有時我去打杯熱水喝,犯人看見了,趕緊跑過去朝我要杯水,我就挨個把熱水倒到杯裏,管教室的犯人一看是我給打的水,就不吱聲了。她們都拿我當親人,有多少犯人在過後的接觸中談到:剛來監獄的時候,心裏一點兒縫都沒有,都不想活了,一接觸你法輪功(學員)這麼幫我,照顧我,我心裏暖融融的,像見到了親人,心裏也有縫了,不那麼害怕了。
在二監區那個監舍裏一呆就是兩年,女人堆,事兒多,重刑犯人堆,壓抑緊張,人的情緒都不好,人又密集,你招她,她惹你,上下鋪幹仗,我在個人生活上一路走來,從未跟人發生過衝突,時刻保持大法弟子的純正、善良、寬容、慈悲,再惡的人,也真沒人欺負過我,身體上遭受的迫害都是在開創學法煉功的過程中造成的,那樣的迫害我是不承認的,這是對大法的迫害,對信仰的迫害。有一次,看我的那個犯人偷走了我手抄的《轉法輪》寶書,交給隊長請功去了,我找隊長要,她不給我,而且也想治治那個犯人,隊長說:她生活有沒有惹著你的地方,只要你說出來,只要有一樣我都收拾她。我一個大法弟子不會因為任何一樣生活中的衝突找大隊長收拾她,隊長很感動,她讓我再抄。我說:如果人人都遵循真善忍做好人,能讓你操那麼多心麼?更不會有這麼多犯人到這來。隊長抿著嘴樂了。
在矛盾中修自己
這些年在家庭中,在與親人的接觸中出現的矛盾很多,很多是多年的積怨造成的,過年時去南方看望八十歲的母親同修時,母親因多年見不到我,就翻來覆去向我訴說,她回老家這二十多年多麼不容易,吃了多少苦,給這個兒子幹這麼多活,給那個妹妹出了多少力,給她伺候幾個孩子,反過來,她這些姑娘兒子怎麼對待她的,很想讓我搬回老家,跟我在一起,還是我孝順就跟我在一起,不用她幹活。
我越聽越煩,越聽越生氣,心想這都是你自己找的,得法了,你不好好修煉,在我最危難時,被關到看守所遭受迫害時,作為母親又是同修,你狠心拋下我不管,視我一雙年幼兒女在苦難中不顧,十八年前,你不老吧,你跟有錢有勢的兒女樂樂呵呵的、高高在上的在看守所告訴我:「你在這好好煉吧,我們過幸福生活去了。」
看到母親現在八十歲的人了,我真不忍心頂撞她了,現在她也學法,聽著母親這些嘮叨,心裏湧起無限的傷感,人世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哪個是你母親,哪個是你兒女」[1],師父的法映入眼簾。
在我的一生中,最需要母親幫我一把時,她卻不聞不問,我對母親的積怨壓在心裏,母親跟我嘮叨,我強忍著,再別跟我說這些了,母親看我這樣對待她,她委屈的哭了,一個晚上,看母親哭的那樣子我很心疼。
我開始深深的向內找自己這顆心,對母親一生的積怨,這是怨恨心,不聽她向我訴苦,真是我錯了,是我不孝順母親,我又跟母親道歉,是我錯了,我應該耐心的聽您訴說,以後我不這樣了。
人世的理是反過來的,我從小吃苦,還有母親對我的磨礪,也許是我前世欠她的,小時候我對母親的付出是車載斗量,是她從小魔煉我堅強的意志力,消去我的罪業,為我得法修煉做了很好的鋪墊。現在我從內心感謝母親從我小時就磨練了我。
我從根本上找到了對母親一生的怨恨心、妒嫉心,妒嫉母親對兄弟、姐妹好,對我不好,怨恨母親不給我看孩子。我找到了這些心,發正念求師父從根本上幫我拿掉它,我要慈悲於母親,鼓勵她好好修煉,珍惜這萬載不遇的在大法中修煉的機緣,跟師父回家。現在我發自內心的感激母親,給予我的人身,我會好好的用這個人身修好自己,圓滿隨師還。
今後我在同修中、在救度眾生中「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誰,先找自己。作為一個修煉者,你要不能養成這樣一個習慣,你要不能夠和人反過來看問題,你就永遠在人中」[6]。記住師父的這段法,真修、實修、下決心修好自己、成就無私無我的正法正覺。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經文:《排除干擾》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忍無可忍〉
[4] 李洪志師父著作:《加拿大法會講法》
[5]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圓明〉
[6]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