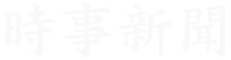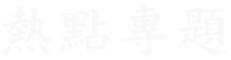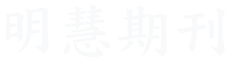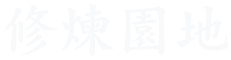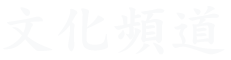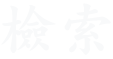學「尖」──科學的誤區
我真的有點反感了。不久後,我意識到她像我的一面鏡子,反映出我的執著:喜歡炫耀和渴望被別人認同。我像她一樣,總是在人的觀念中找藉口,喜歡安逸,或為自己的錯誤開脫。她問我們學大法以後,發生了甚麼變化。聽起來像:「如果我學大法,我會得到甚麼?如果我花努力看這本書《轉法輪》,我會有甚麼收穫呢?」這其實也反映我們自己的問題。
那天晚上,我在明慧網站上讀了一篇修煉交流文章,其中提到學員應看一看自己學法的動機。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思考為甚麼要修煉和讀《轉法輪》。我接受了這個建議,仔細的剖析自己修煉的原因。特別是大約三、四個月以來,我不能和大家一樣,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直到七點或八點才起來。自從我看到自己的執著已經兩個月了,但仍無法突破。
其實,我走進大法修煉是因為我發現這些知識令人著迷。此外,我想了解更多。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學法帶有很強的目地性。除此之外還隱藏著這樣的執著:學法會使身體更健康,這促使我更想多了解法,這樣我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我明白我必須清除這些執著,不能帶著有求之心來學法,說嚴重點,這簡直是有點欺詐性質,這可不行。
師父說:「對小孩教育的時候,大人往往為了他將來在常人社會中能有立足之地,從小就教育「你要學尖一點」。「尖」在我們這個宇宙中看就已經是錯的了,因為我們講隨其自然,對個人利益要看的淡。他這麼尖,就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誰欺負了你,你找他老師,找他家長」,「看到錢你要撿」,就這樣教育他。」[1]
我從小家人就教育我要好好學習,這樣,長大後我可以生活得好。我還被教育,用某種方式來做事,這樣我就會獲得更多。我正是用這種思維方式對待大法修煉的。正如師父所說,我被訓練成「尖」,還抱怨別人。當我用它來對待法時,我是尖還是傻?
師父一九九六年在悉尼講法的時候說:「你比如說現在這個科學它不能證實神的存在,它不能證實另外空間存在。它看不到另外空間的生命和物質存在的形式;它也不知道人類有道德這種物質在人身體上的體現;它也不知道人類還有業力這種物質在人體周圍的表現。那麼人們都相信現代的科學,現代的科學證實不了這些。而且一談起道德善惡之事等科學以外的東西都視為迷信,實質上不就是掄起了現代科學的這個棒子,去打我們人類最本質的東西──人類的道德嗎?是不是這樣?因為它不承認也證實不了德的存在,它就說它是迷信了。」[2]當我想到我學習大法的初衷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就掄起這根棍子了──這根棍子叫科學。
我在東歐的一個國家長大,經歷了柏林牆的倒塌, 在一九九一年完成我的學業。在那段時間裏,人們經歷了很多焦慮。如果一個人找不到正確的用詞或者不能提出正確的理論,就會被認為愚蠢或者是騙子。我想方設法做好,學會在適當的時候大喊「是」。我還學會了保持低調,不評論誰好誰壞。我相信科學永遠不會錯的──因為它可以被證明。是的,它的理性,可以被證明。
我過去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還為我的學識和對推理事物的能力感到自豪。我想了解更多,這樣,我的智慧會得到肯定。隨著多讀一本書,作進一步的研究,作一份科學報告和學習一個新的定義,我的知識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我失去原來的真正自我,直到有一天我不再知道我還有真正自我。
學大法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但是我的世界觀還沒有改變。一個修煉人必須學好法,隨其自然,放棄人的觀念。因為法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不是科學或人的甚麼東西。
我意識到我對「隨其自然」[1]的理解是不對的。我曾經認為「遵循自然的規律」意味我們隨著面前的展開的路走。我在年輕時所受的教育是,「自然」意味著這是它必須的方式。這種「自然」是由現代科學決定的。然而,從法的角度來看,遵循自然的過程,意味著為過去的錯誤行為而受苦,並消除業力。承受痛苦並不容易,我過去認為的簡單的生活方式是偏離法的,是錯誤的。
簡而言之,我過去認為的所謂的自然就是我們目前的生活,而不是更長遠的看待生命的過程。
我想說在認識到科學的誤區後,我解決了在早上起床煉功的問題。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悉尼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