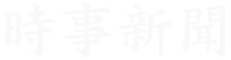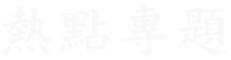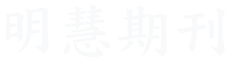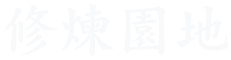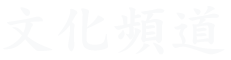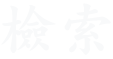從辦護照的經歷想到的
我來日本以後,一直在參加很多的講真相活動。不光是因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肩負的責任和使命,還因為我已身在自由世界,監獄裏一起受迫害的同修卻仍然在巨大的承受之中,有的釋放以後不久又被抓進黑牢,他們的處境歷歷在目,有的在多次入獄後被迫害慘死。時間如水流失,世人皆在險境,這些都讓我不敢也不忍懈怠。
我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就有公派出國的機會,被家事牽絆而錯過了師父安排的機緣。二零零六年以後的幾年間,再次有了出國工作的機會,廣告不讓進門的小區卻在我家樓下門洞前的草地上奇怪的豎起了一個「憨瑞出國」的廣告牌,但是我在幾年的時間裏都沒有悟到師父的點化,同修和娘家人也一致反對我出國而再次錯失機緣,一直到在監獄裏度日如年、被迫害了兩年以後,我才如夢方醒。
我來日本,是在多年好友的美國同修鼓動下出來的。當時我的身體和頭腦都已接近崩潰。我在兩次申請美國簽證失敗以後來到日本,打算經日本去美國,但是第三次簽證也失敗了。同時好友說話越來越奇怪,我才發現,好友去美國嫁的丈夫是明慧網十幾年前就公布過的中共特務。所謂「好友」對我的關注從一開始就有不可告人的目地。
有時候我還碰到中共派到海外的特務,有一次有一戴墨鏡身材高大看起來像國安的人混在遊客中走到真相點,經過我身邊時,他聲音低沉的對我說,「還有家人在國內呢!?」有一次發神韻單張時,兩個中國人隱蔽的對我胸前掛的姓名牌錄像,我若無其事的走過去把單張遞給他們,他們神色慌張扭頭就走。有一次有一人像是便衣國安特務,混在遊客中眼神極其兇惡的盯著我看。我走過去對他講真相,他不聽反而狠狠的威脅我。
向日本的華裔同修請教換護照的流程,同修善意的提醒我說,「你一定要把難民紙拿下來。」有位同修說,「申請難民的理由多種多樣,你拿到難民紙他們就不太會注意到你是法輪功(學員)。」
但是我不想拿下來。拿下難民紙除了顯示出內心的怯懦,甚麼作用都不會起。在國內我都不怕,在國際社會我為甚麼要怕它?還是放下心來,把一切交給師父吧,相信師父一定會給我最好的結果。
說來也巧,在我去申請的那天,一出地鐵,碰到一位見過兩次面的外地同修,她要去大使館辦理香港簽證,正好可以幫我發正念。我們拍照、填表,坐在大廳等叫號。當叫號跳過了我的號碼,叫到我後面的人時,我直接走到窗口,說應該輪到我了。工作人員愣了一下,隨即和旁邊窗口的工作人員商量了片刻,就把我的材料收下了。事情辦完時間還早,我在國會的項目請了一天假,已經安排了其他同修替我站在國會門前,於是我走出大使館,就到門前小馬路對面的真相點和老阿姨同修一起煉功和發正念了。
轉眼到了取新護照的時間,我走下地鐵,還沒找到出口呢,又碰到一位見過面但是從來沒有講過話的本地同修,也是去辦香港簽證。她從後面叫住我,帶我走一條近點的路。聽說我是去領新護照,就問我,「難民紙你拿下來沒有?」聽我說是有意沒有拿下來,她很吃驚,替我擔心道,「以前護照到期根本不給換,有段時間很多大法弟子都沒有護照了呢。」還說她自己辦護照的時候,工作人員拒絕受理,她給他們拍了錄像據理力爭,吵到領事出來以後才給辦了。我說以前是以前,形勢天天都在變。也沒有請她幫忙發正念了。
人很少沒有排隊,我交了錢很順利的把新護照取到了。
時間還早,我走出大使館,又到門前小馬路對面的真相點去煉功和發正念。整個過程心態很好,心情很平穩。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下午結束的時候,捲起條幅收好東西,我向對面大使館聘請的日本警察鞠躬致謝,對方也微笑著向我回禮。
二零一六年元旦期間,我們在靖國神社附近發單張和做「訴江」徵簽,走過一群中國大陸來的學子,看年紀大約是博士生,他們邊走邊感慨道,「人心變了,世道也要變了!」現在又是一年快過去了。
現在真相點上人來人往的遊客中,除了當初賣力參與迫害法輪功欠了血債的人,出於對清算的恐懼和自身的利益還在擁護邪黨以外,已經沒有甚麼人為共產黨辯護了。特別是江澤民,最普遍的評價就是:「沒有一個人說他好!」就算是體制內領工資或退休金的人,那些還在臉紅脖子粗堅持為共產邪黨站台的中毒太深的愚民,連他們一起出來的朋友都嫌他們背時倒灶的,思想落伍太跟不上時代了!
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日子裏,衷心的祝福世人,珍惜大法弟子的辛勤付出,給自己定一個美好的將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