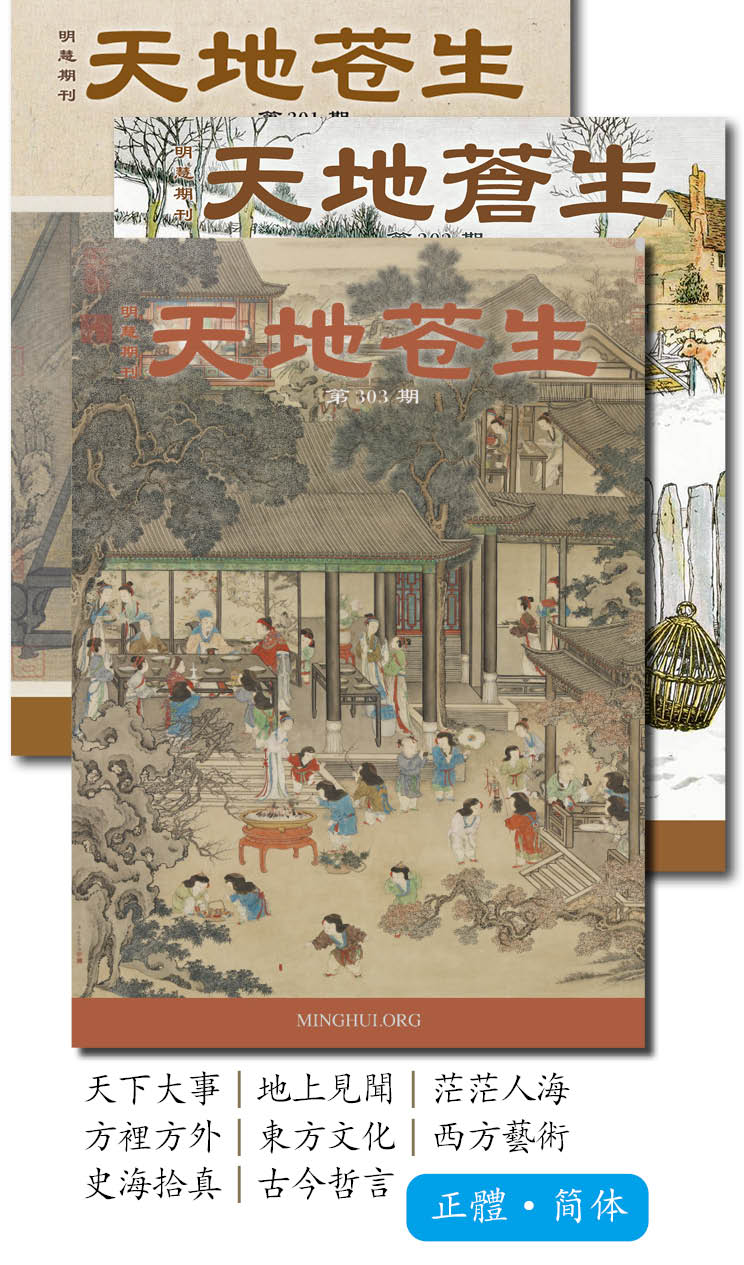曾遭非法勞教、酷刑折磨 瀋陽工程師控告元凶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當時四十三歲的胡林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胡林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一、在派出所遭毒打、刑訊逼供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我發真相資料,被綁架到瀋陽市皇姑區淮河派出所。當時已是半夜,一個警察就喝令我蹲著,我不蹲,他使勁把我摔在地上,後背著地,開始用電棍電我,當時我戴著背銬,手銬深深的紮到了肉裏。後來對我進行審訊,直到後半夜。然後把我雙手銬在暖氣管子上,派兩個協勤人員看著我,不讓我睡覺,閉眼睛也不行,就這樣我一直睜著眼睛坐到天亮。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
第二天白天,幾個警察繼續對我進行非法審訊。把我一隻手銬在凳子上,又不讓我坐在凳子上,身子又站不直,我只能歪著身子站著,用這種方式折磨我。旁邊放著電棍,多次電我。夜裏,為逼我說出其他人,又對我刑訊逼供。兩名警察夥同兩名協勤人員強行把我綁在椅子上,其中一個警察(據說是副所長,身高一米八以上,滿臉橫肉,膀大腰圓)掄圓了膀子打了我十多個嘴巴子,我感覺腦袋嗡嗡的,臉被打得腫起來很高。緊接著,又用拳頭猛擊我胸口,連續打了十幾拳,他的手被震的很疼,打完後不停的甩手。又用電棍長時間電我全身,哪敏感就往哪電,膝蓋、手指尖、腳趾尖,甚至生殖器都電到了。他們還把大蒜搗碎了抹在我的眼睛上,故意用香煙熏我。最後,他們用盡了種種邪惡手段,一看我甚麼也沒說,只得罷手,又派兩個協勤人員看著我,不讓我睡覺,他們自己則灰溜溜的走了。
第三天白天,又把我一隻手銬在凳子上,繼續對我審訊、電擊、折磨。到了下午,組織了所謂的「材料」,把我送到了瀋陽市皇姑區看守所。
在派出所兩天兩夜的時間裏,我沒睡一點覺,沒吃任何東西,渾身上下到處是電擊後留下的黑點,臉被打得腫得很高,手也被手銬勒得腫起來,像饅頭一樣,有個警察還假惺惺的告訴我手舉起來能消腫,我沒聽他的,他就用電棍電我。
二、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在瀋陽市皇姑區看守所,因我拒絕在警察面前蹲著和不背監規,我所在監室姓陳的獄警氣急敗壞地給我戴上一種稱為 「約束帶」的刑具, 由很粗很硬的牛皮製成,像腰帶一樣繫在腰上,多出兩個環套在手腕上,用螺栓擰緊固定,雙手基本動不了,小臂只能平端著,像捧著東西一樣,俗稱「手捧」。由於手動不了,沒法洗漱和大便;吃飯時頭和手同時使勁才能把食物勉強送到嘴邊;睡覺時只能平躺著,雙手舉著,沒法翻身。我連續戴了15天,全天二十四小時戴著,吃飯、睡覺、上廁所也不鬆開。由於手動不了,沒法洗漱和大便,我15天沒洗漱、沒大便。
到了第十五天,陳獄警把「約束帶」給我打開了,我才得以大便、洗漱。誰知幾個小時後又給我戴上了,這回又多了一副十八斤重的腳鐐,又連續戴了15天。走路時腳鐐上得拴條毛巾用手提著,雙腳在地上蹭,才能勉強行走。睡覺時雙手舉著,由於腳鐐太沉,腳也動不了,沒法翻身,基本上只能一動不動的平躺著。
幾個月後,我遭非法勞教兩年,被劫持到瀋陽張士教養院。
三、在瀋陽張士教養院和洗腦班遭受多種酷刑折磨
張士教養院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由程殿坤(張士教養院政委)全面負責,宋百順(張士五大隊教導員)、史鳳友(張士洗腦班的主要負責人)是主要執行人和打手。對不放棄信仰的每位法輪功學員採取種種酷刑長時間折磨,邪惡手段令人髮指,真可謂人間地獄。
我因不放棄信仰,遭受過多種酷刑,主要如下:
毒打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送到在瀋陽市鐵西區精神病院辦的洗腦班。我因絕食抵制迫害,史鳳友狠狠地打了我幾個耳光,打得我嘴角流血。又讓人將我按到床上,用疊在一起的床板猛擊我臀部,床板折斷,臀部被打成紫黑色。
 中共酷刑示意圖:毆打 |
還有一次,因我拒絕蹲著,十來個人將我強行按到地上,多人像瘋了一樣用腳猛踢我的大腿跟部,成紫黑色。
捆綁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瀋陽市鐵西區精神病院洗腦班,十來個人一起動手,把我按到地上,雙腿伸直,將我後背向下壓,幾乎與腿挨在一起,然後用床單把我的上身與腿牢牢綁在一起,一動也不能動。這樣綁了大概幾個小時,當時痛苦程度無法想像,真是生不如死。
 中共勞教所酷刑演示:捆綁 |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張士教養院小樓,法輪功學員鄭守君(現已被迫害致死)也遭過此酷刑折磨,被捆綁了三、四個小時,以致之後三個半月無法正常行走,腳和腿錯位,變得腳心朝上、腳踝骨著地。「走路」時,必須有人攙扶才勉強能動。
長時間罰蹲、罰站
這是張士洗腦班經常採用的邪惡手段之一,我多次遭此酷刑折磨。強迫我長時間蹲著,有時連續蹲一宿,甚至更長時間。吃飯時也不讓起來,蹲著吃。隨著時間的延長,每一分鐘都疼痛難忍。在忍著身體疼痛的同時,還必須接受強制洗腦。
有時強迫我長時間站著或頭頂牆站著,一站一宿,有時困的迷糊過去了,差點摔倒。
電棍電擊
二零零二年九月,因我拒絕按手印,在張士教養院四大隊生產車間,警察史鳳友夥同另一名警察,當著全大隊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將我用繩子綁住按倒,用電棍電擊我的頭部及其它部位。與我同在一個大隊的法輪功學員劉憲勇勸其停止行惡,史鳳友上前將劉憲勇踹倒,命令普教將他綁上,對他進行長時間電擊。
野蠻灌食
 酷刑示意圖:摧殘性灌食 |
為抗議對我長期酷刑折磨和強制洗腦,我絕食抵制迫害。在五大隊,我連續絕食二十天,每天對我進行兩次野蠻灌食。警察指使犯人將我強行按住,將管子從鼻孔插入胃中,有幾次可能插到氣管裏了,我感到喘不上氣,險些窒息而死。後來將我轉到一大隊,灌食方式更加野蠻。十來個犯人把我強行按在地上,用鋼匙、筷子把嘴撬開,大雪碧瓶子剪去一半插進嘴裏,在玉米糊中放了大量食鹽,連續往裏灌,我險些窒息死亡。法輪功學員陳松、劉憲勇都曾被野蠻灌食。
剝奪睡眠
在張士教養院和洗腦班,對於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每天只能睡二、三個小時的覺,天天如此,甚至不讓睡覺。我曾連續多日每天半夜兩、三點鐘才讓睡覺,早上五點鐘就得起來。
二零零二年十月左右,在張士小樓,在史鳳友的授意下,連續十五天不讓我睡覺,並同時進行強制洗腦,我一直坐著,幾乎一眼未合。法輪功學員杜江和李滿心也都曾連續多日不讓睡覺。
多人圍攻、強制洗腦
這是張士教養院最常用的邪惡手段,持續數日,天天如此,只要不轉化就不停,同時伴有罰蹲、剝奪睡眠、捆綁、毒打等,對人的精神、肉體造成極大痛苦和巨大傷害。
我也曾長期遭此手段折磨,幾個人一組三班倒,長期、連續做我的所謂「轉化」工作,強迫我與他們進行所謂「交流」,保持沉默也不行。如不轉化或不配合,就長時間罰蹲、剝奪睡眠或採取其它迫害手段。
遭奴工勞役
二零零二年,我和其他幾名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被送到張士教養院四大隊,強迫我們和犯人一起進行奴工生產,分配和犯人一樣的任務,白天幹不完帶回監舍,晚上繼續幹,有時幹到深夜。這裏生存環境、衛生條件極其惡劣,每天吃著最差的飯菜、從事著長時間、高強度、超負荷的奴工勞役。四大隊主要生產一種出口的髮梳和包裝盒(稱為插皮子和糊盒)。髮梳頭由橡膠做的,糊盒用的膠水是一種化學製品,發出嗆人的氣味,這些對人體都有害。
我主要是糊盒,有時也插筷子,就是將方便筷套上紙袋或塑料袋,上面印有「已消毒」的字樣,其實根本就沒消毒,而且很不衛生。
由於我長期受迫害,加之衛生條件極差,二零零二年冬天我身上長滿疥瘡,不斷的往出淌膿血,無法穿棉衣棉褲,只得穿一條單褲、披一件大衣,光腳穿著拖鞋。即使這樣,四大隊教導員馮樹林、大隊長梁某還強迫我出工。宿舍和生產車間不在一個地方,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外面集合,北方冬天,寒冷程度可想而知。
四、再次被綁架、抄家、打傷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晚六時左右,在瀋陽市國保大隊的指使下,新民市公安局西北街派出所、新民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瀋陽市皇姑區警察,強行闖入我在瀋陽的出租房中,將我和當時正在我家作客的法輪功學員潘友發打傷。並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和搜查證的情況下,強行抄家,共抄走現金近萬元,銀行卡、存摺多個,台式電腦一台、筆記本電腦兩台,以及大法書箱等大量私人財產和物品,用卡車裝了一車。
綁架過程中,瀋陽市皇姑區怒江派出所警察王德剛(怒江派出所現已解體,歸到塔灣派出所)將我撲倒在地,壓在身上。一名警察用掌猛擊我的頭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滿臉是血。非法抓捕潘友發時,瀋陽市國保支隊警察陳福洋用刀將潘友發的手臂劃傷,並用右拳猛擊他的軟肋,然後抓住潘友發的頭髮就往牆上狠狠地撞。警察欲製造案情立功,反誣陷潘友發持刀傷人,將刀拋擲樓下。
綁架我們下樓過程中,我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並拒絕上車。一名警察用掌猛擊我的頭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右眼嚴重充血,滿臉是血,鼻腔、口腔中也是血。然後,強行將我抬上車,並用膠帶將我和潘友發的頭部、胸部和腿部固定,戴上頭套,開車送往新民。整個行程兩個多小時,我們全身無法動一下,又戴著背銬,痛苦至極。
 中共酷刑示意圖:背銬 |
到新民後,警察又連夜對我和潘友發進行非法審訊,直到凌晨三點結束。在我強烈要求下,才給我鬆開背銬,戴背銬時間長達九小時,手銬已深深勒進肉裏,雙手腫脹,雙手手腕兩側血肉模糊,傷口多日無法癒合。
第二天將我和潘友發送往新民市看守所非法關押。在我的強烈要求下,對我身上的傷進行了拍照、存檔。在看守所我絕食抵制迫害,因擔心我出現生命危險,才將我放回。現在我被迫流離失所,並且單位停發我的工資和一切待遇。
被告人江澤民親自操控並實施的這場迫害給我及我的家人精神上、身體上、經濟上都造成了無法形容的巨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