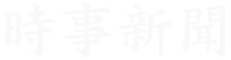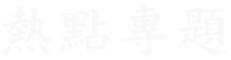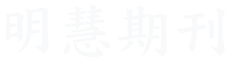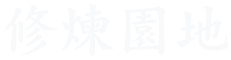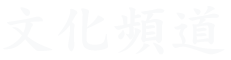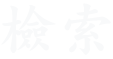我被上海女子監獄迫害的經歷
「轉化」真相
我沒有被關進新入監區,而是直接被關進一個牆上貼厚厚的板(起隔音作用的)、沒有窗,只有像雙人床大小的封閉小屋,睡在地板上,頭右側一臂之遙,放個痰盂當馬桶用,吃喝拉撒睡全在這小屋裏,五個包夾犯人,二人一班,二十四小時輪流對我進行「轉化」迫害:他們三個多月不許我洗澡,不許換衣服,每天五點多起床罰站、罰靜坐,同時強制看和聽污衊大法的錄像、錄音,不許與家通信,家裏來信也不許看。
我拒絕放棄「真善忍」的信仰,孩子每星期到監獄一次要求見我,均被拒絕。獄方還剝奪我的申訴權。
包夾經常將我推搡、摁在地上折磨,用硬紙膠做成彈子用皮筋射我,我的胳膊、腿、手被打得青紫;包夾韓月還用裝滿花露水的瓶子打我的頭,疼了很長時間,我每天都被包夾施用各種手段折磨、打罵,我寫信向領導層反映,獄方沒有回音,包夾也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為逼我「轉化」,獄警給我女兒家寫信說要讓她婆家、丈夫知道我被關押在監獄的事,並挑撥我女兒離婚,她們把信寫完將信念給我聽,用來脅迫我,但沒得逞。
有個五十多歲、患高血壓、心臟病的包夾,後來不參與迫害我了,對我好了,她被別的包夾訓斥、誣告,用尺把她胳膊打得一道一道的血印,我當時不忍心她因為我挨罵挨打,沒看透是騙局,被騙寫了犯人寫的幾書,後來她們又逼我「悔過」我才知道上當了,也驚醒了,堅決表示絕不會「轉化」,她們像瘋了一樣,連罵帶打,把我的東西扔了一地,我寫給女兒的信也被她們搶去,還以不倒痰盂為由刁難,二十多小時不讓我上廁所。
正值七八月,烈日炎炎,惡警們的房間和值班的都是門窗對流,還配有電扇,我這沒窗子的小號,門僅距離另個監房牆不足一米遠,不通風,也沒有降溫設備,一面牆還被太陽整個烤著,加上痰盂發酵的味,使我悶的喘不過氣,頭暈腦脹,汗流浹背,連睡覺的席子都是濕的,起了一身痱子。牆上貼著污衊師父的話,還拿來師父的像抽打罵我,還把師父的像扔在過道上任人踩,並把我架起來,往師父像上墩,逼我踩。有警察撐腰,她們更無所顧忌,號長韓月揮拳把我牙打掉,另一包夾用尺把我手指打裂,渾身被打的都是傷,後背熱辣辣的疼了好多天。
號長韓月傳達警察指令告訴包夾:「施中隊說了,別死就行。」說這話時根本不避我,就這樣在別死就行的指令下,各種折磨也來了,靜坐腿中間夾個小本,無故罰多站,往後延時間,還把我腿扎破,說打就衝過來打。
酷刑「約束刑」
後來她們達不到「轉化」我的目的,把我轉到四監區。
到四監區第一天,我就向警察談了修煉後身心變化,明確表明不認罪,在這裏我住上了床,這也是在女監幾年僅享受一個多月的待遇,三個犯人看管我。在五監區被折磨的情況在這裏依舊延續著,後來我出現了頭昏腦脹症狀,包夾怕擔責任讓我去檢查,我考慮講真相,就同意了。
從此惡夢隨之而來,他們說我血壓很高,我沒有配合他們的所謂的「治療」,我給他們講述了自身修煉法輪大法後身體的神奇變化實例,向他們講真相並表明我這不是病,是被迫害的,不吃藥。結果被惡警上「約束刑具」,七天七夜,睡覺都躺不下。
我考慮她們受中共造假宣傳矇騙,決定藏藥,用事實來說話,藏藥第二天我的血壓幾乎正常,以後每天量,逞下降趨勢,一個月後我拿出藥和盤托出此事。我想用事實向她們講法輪大法的真相,但她們根本不聽,更不允許我講,給我上「約束刑具」,全然不顧我已六十多歲年齡。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上刑、關禁閉處罰。隊長張某說:不「轉化」與六一零聯繫,讓你女兒別上班陪你到「轉化」為止。用株連手段恐嚇威脅我。
罰站折磨
每天從早五點多罰站到晚十一點半。我被折磨的雙腿粗腫,不能正常站立,只能九十度彎腰, 要想能站平衡,雙手抓住兩邊衣襟,撐住腰,還得往前挺肚子勉強站立。
高分貝折磨
我還被戴上耳塞強迫聽所謂監規,從早七點十分聽到晚九點多,只有午、晚飯拿下五、六分鐘,一天十幾個小時,把音量放大到極限,戴上後,我就噁心欲吐,他們給我上板刑時都不拿下耳塞,耳塞聽壞了四副,她們就用我賬上的錢賠的,一個多月的音量刺激,導致我聽力明顯下降,到現在還沒恢復。
飢餓折磨
見我仍不屈服,他們又以飢餓來折磨我,一頓只吃半飽的飯量還要分成三頓吃,葷菜全無,素菜只幾口,還必須用水沖洗過後沒有鹹味才允許吃,喝水上、下午各一遍只給幾口水,而且必須是涼的。這樣的折磨,我胃難受直吐水,駐監檢察官來,我揭露了此罪行。監區警察沒料到,我不低頭還向檢察官告狀。大隊長宋某來了,把我推倒在地,告訴包夾飯再減少。就這樣每頓飯只剩下可數的飯粒了,為預防疾病,規定門窗是開著對流的,已是成冰的冬季,年輕的包夾穿著棉裝,懷裏還抱個熱水杯,六十多歲的我,因不放棄信仰不認罪,被強迫穿單衣服,單鞋還被飢餓折磨,凍的我身體不停的顫抖,卻因為顫抖被訓斥、記違紀,還因為我用紙塞過耳減少音量刺激為由,上廁所不讓用衛生紙,每次我只能抻扯穿在身上的襯衣替代衛生紙用,卻被記違紀。
不讓洗澡
我還被長時間剝奪洗澡、換衣的權利,頭,身上,散發難聞氣味,每天被包夾侮罵,
後來,他們還逼我刷擦廁所,刷完不許洗手就吃飯,每天都這樣髒兮兮的拿勺捧碗吃飯,別人的碗是集中放的,用開水沖泡,我的碗只能放在我臉盆裏,與毛巾,腳巾洗衣粉肥皂放一起,飯後,包夾給小半碗涼水沖洗,多次不准出來洗碗,只好放禁閉間地上,像乞丐一樣,頭頂著髒兮兮的要飯碗睡覺,甚麼衛生、預防疾病規定到我這全無。
包夾每天侮辱我、折磨我,監區獄警經常獎勵她們毛巾、牙膏、衛生巾、吃的。牆上貼了上下兩層,大半開紙關於我的「違紀」和侮辱醜化我的大字報。
不讓睡覺
由於我長期被酷刑折磨,還要被凍、飢餓等迫害,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除了身上的傷痛,小腹和下身經常疼痛,一次曾痛的我出現昏睡狀不知過了多久,包夾怕擔責任,後半夜把警察叫來,任包夾把我身體掐青腳踩腫,我依然難睜雙眼,圍著我踢打,沒有任何人制止。
他們見種種折磨我仍不屈服,罰我每天半夜兩點以後睡覺,有幾次都凌晨四點了,才讓我躺下,一個小時後就被弄醒。
潑水折磨
我終於被折磨得不能行走,卻被強迫行走,使我摔了一個又一個跟頭,大隊長又以我爬起來慢,告訴包夾往地上潑水,我的雙腳泡在水裏,我只好拖著不聽使喚的雙腿,用抹布把水一點點擰在盒裏,天天重複如此的折磨,直到我有一天重重的摔在牆上,頭破血流,才停止「潑水刑」的折磨。我頭上的傷口一個多月才好,牆上血還清晰可見。
酷刑「上板」
我仍不「轉化」,惡人把我拎到辦公室,隊長張某、大隊長宋某,把我下身扒光,大隊長宋某直接用電棍電擊雙腿,痛的我在地上爬!我還是不認罪,讓我躺板上,宋某、張某逼我寫保證,沒達到目的,告訴包夾動就捆上,這樣我被上了酷刑「上板」,全身被牢牢綁在地板上動不得,全身僵直和板合為一體,我現在都形容不了那僵直不動的滋味。
 |
再遭飢餓
二十多個日日夜夜,我被迫寫了:獄內不煉功,不背經文,不弘法的保證。我徹底癱了,下了刑之後,不能站立,只能雙手扶牆加上身體貼牆上,一點點挪動,幾個月以後,才一點點恢復走路,腳被板硌的結了厚厚的痂,半年以後才被我一點點扒下痂皮,現在還留有疤痕。
警察目的達到了,又安排了親情接見,孩子爸見我就哭了,孩子驚訝幾個月不見怎麼瘦的脫了人樣,五監區中隊長施某說我像骷髏。半年的飢餓刑罰非人的折磨,我的體重從一百二十斤降到七十六斤,這還是穿衣褲鞋稱的重量,整整五十斤哪!
被迫妥協後的我,心如刀絞,我清楚的知道:愧對師父慈悲苦度!我沒罪,不允許這樣迫害繼續!遂以行動反迫害證實法,結果剛恢復一個星期的飯量被減,包夾把我牙床打腫,還被要求走隊列,午後二點多才放回吃飯,晚間別人都洗完碗了,我才回去,晚新聞後又被拽出去,走到午夜十二點。
她們還經常在我睡著時壓我腿,或掀被折磨,把我驚醒,用這樣手段來阻止我以達到不讓我睡覺的目的,在減飯的基礎上,包夾還剋扣,我曾餓的利用掃廁所之機,翻找垃圾裏的菜根吃,被發現後垃圾筐被拿走。
遭電棍電擊
他們還規定飯前要唱幾首邪黨歌,否則不許吃飯。我就唱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張、黃兩隊長把我弄到沒有監控的屋子電我,他們嫌電量小,又拿來一個電棍往我身上潑水電我!
有一天他們把我弄到辦公室,大隊長宋某、隊長張某圍著我,黃某拿著電棍問我:你說法律大還是你法輪功大?我大聲回答:大法大!
又一輪迫害
這期間,我寫了嚴正聲明,聲明所說所寫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廢,準備交給隊長,放在被裏,後被搜去,我絕食反迫害,我不承認服刑身份,不報號,不配合一切,她們以不放床板、不許我睡覺逼我屈服,夜晚我只能躺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她們撕扯我不讓我睡,還往地上潑水,痰盂被拿走,不許如廁,我憋不住不得已尿在地上,包夾就把我的衣褲毛巾毛衫臉盆等物都扔在尿液上……
警察惡犯這邊無休止的這樣迫害我,那邊卻給我女兒打電話,說我又在裏邊鬧,還往地上尿。
被關禁閉一年多
一次包夾把我倒著頭朝下拖出禁閉間,大隊長把我弄到廁所,舉著電棍恐嚇威脅,見我仍不屈服,沒動我。幾天後我被送到醫院。
從醫院回來,又回到小號。在探視時因為我告訴孩子按真誠、善良、忍讓做人,被惡警要求寫保證,不再宣揚法輪功,我不寫就停止接見,不久又以飢餓來迫害,包夾也藉此刁難,警察不許我說任何話,往我嘴裏噴暗紅色液體,我窒息般倒地,捂著胸在地上滾,大隊長宋某和隊長張某命人把我拖到禁閉間,我喊「法輪大法好」,大隊長黃某威脅說:這是獄內犯罪。檢察官來時,我反映獄方以飢餓等酷刑逼我絕對服從,後來給我恢復了飯量,但禁閉沒解除。
我不再承受一切,惡人在放污衊大法的錄音時,我就大聲揭露中共製造天安門自焚假案,藏字石天意,我唱大法弟子歌曲,喊法輪大法好,我也不再承受冬天在禁閉室挨凍、不許洗澡,我指著監控人員高喊:這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後來他們同意我與其他人一樣去浴室洗澡,我不參加任何學習,不背監規,不報告,後來監獄著火了,我才得以走出禁閉室;不久又因不報告、脫囚衣,被大隊長黃某上刑,我大喊黃某執法犯法,她把我棉衣褲扒去,穿單衣凍我,又被黃大隊送進禁閉室,我煉功被包夾抻胳膊壓腿壓在地上。
在監獄的三年零兩個月時間,我因堅持信仰被關禁閉一年多,幾次被上約束刑,使我胳膊受傷,活動疼,腰腿也經常不適,胃也經常難受。
上海女子監獄獄警縱容惡犯欺壓、打罵虐待我,而包夾犯人執行獄警指令折磨、打罵我之後,都獲減刑假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