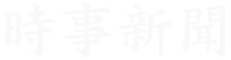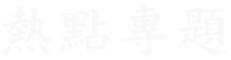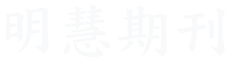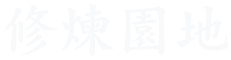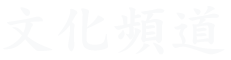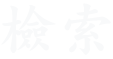河北老人李鳳珍八年五次遭綁架 幾度被害致命危
我叫李鳳珍,九八年底開始修煉法輪功,原有的肺結核、淋巴結核、冠心病、腦血管硬化、腰肌勞損、左側輸卵管化膿、神經官能症、兩腿不能正常走路、虧心虧血等病症,學法半個月後,所有病痛一掃而光,身體神奇般康復,心胸開闊了,說話和氣了,對人寬容了,身體一身輕,我逢人就講大法好!然而,就在我得法不到八個月的時候,邪黨對大法的迫害就開始了。
第一次被綁架:遭非法關押四天
九九年「七二零」迫害一開始,我就被當地邪黨惡徒綁架到建昌營鎮大院關了四天。在被關押期間,我把我的親身感受說給那些逼迫我放棄大法修煉的人聽,他們真的聽了,也同情,還有人當我面說:「大法真那麼好,等以後消停了,我也看看大法書。」惡徒最後威脅我說:「別比手劃腳做動作,回家自己修心」,就把我放了。但鎮裏人威脅家人施壓於我,使我不得安寧,身心受到摧殘。但我一顆跟隨師父、堅修大法的心反倒更堅定了。我看到一個人越變好、變善,當今的社會就越容不下你,這裏真壞透了。好好修,離開這,好人有好歸宿是天理。
第二次被綁架:寫兩封勸善信被關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八月,遷安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長彭明輝、科員哈福龍把我綁架到遷安市看守所,原因是我寫了兩封信給建昌營鎮政法委書記全志寶,信中寫了不叫大法弟子做真善忍的好人是幹蠢事,是對社會的安定、家庭和諧、人民身體健康都犯了大罪,學大法的人都是好人,安分守己,比你們這些當官的可好多了。就因為寫了四頁紙的大實話,我被非法拘留,關進看守所。我在那看到被關押數月的同修白雪霜,她被看守所副所長惠志江用皮帶打的身上紫黑色;還有高建華、王韋月,她們被戴上死囚犯的大腳鐐,惡警逼她們上下爬樓梯,逼她們在操場上跑,戴著十多斤的大鐵鐐哪能跑的起來呢,不跑就用皮帶抽打,她們的兩腳腕子被磨破,淌著血水,可是遷安看守所的惡警惠志江、雷顯生一邊打一邊笑,人性全無。
我進看守所第二天,我們四個同修開始絕食抗議,堅持八天,她們三個又都有傷,一看太虛弱,就把我們四人都放了。可是遷安邪惡六一零辦公室主任又迫害我,逼不了我們修煉人就逼著家人寫不煉了的保證,同時政保科科長彭明輝還逼家人拿三千元錢做保證金。
第三次被綁架:被迫害致奄奄一息
二零零零年九月末,我回家才兩個多月,就又一次被遷安公安局政保科科長彭明輝等綁架,理由是我想去北京上訪了,可是我根本沒出遷安市,就又判了我十五天拘留,我不簽字,絕食絕水抗議,結果八天無條件釋放,但是我也奄奄一息了。
第四次被綁架:被害的鼻嘴噴血沫子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我身體還沒復原,又被建昌營鎮鎮長金士強與建昌營鎮派出所惡警趙某某押送到遷安市城南劉季莊洗腦班。當時洗腦班由遷安市委負責人、惡黨徒張來儒主抓,邪惡之徒:李福永(市委組織部)、寧學軍、王永進(市委宣傳部)、楊秀麗(市委宣傳部)、張某(市司法局)、蘭田(市體委)、劉部長、楊玉林(原市政府辦公室主任)。大約三、四十人看著二十左右大法學員,每天吃五兩糧食,基本半飽也吃不上,強迫跑步,強迫聽共產邪黨造謠、栽贓的宣傳片子;不配合他們的學員就被罰站,各種姿勢的體罰,打罵是家常便飯,絕食抗議惡人們就野蠻灌食。
我就被惡人們灌了四、五次,牙被撬掉一顆,插管時就插進了氣管,我被惡人們害得鼻嘴往外嗆血沫子,惡徒楊玉林卻說明天還灌,醫生說一個星期內都不行,已經有內傷了,說完就走了。後來我對這幫邪惡之徒說:還有甚麼招都拿出來,惡人們也無可奈何,也不叫我們跑步了,也不叫我們看造謠的光盤了,我開始吃飯了(實際應該絕食抗議直到放出我們為止,當時就沒悟到)。結果三天後我就被送到遷安市看守所。
在遷安市看守所遭非人折磨
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我和其他幾位同修堅持背法煉功,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惡警給我們四個女同修戴上十七、八斤重的大鐐子。其中就有一個同修後來被判了兩年勞教,在開平勞教所被電擊、毒打,導致腦出血,最後死亡的裴翠榮,她也只是在天安門前喊「法輪大法好」才被勞教的。大約有兩個月左右時間吧,我們煉功的幾個同修幾乎黑夜、白天的被吊銬在鐵門或鐵窗上。一個晚上一個同修有尿,惡警張山就是不給解手銬,差點沒把膀胱憋壞,因為手瘦小,慢慢退出手銬,用一個塑料盆接著也尿不下來,膀胱都不會收縮了。我們說別緊張,慢慢的一滴滴才尿下來,一泡尿足足用了半個來小時。看守警察白天向看守所其他人反映此事,也沒作任何解釋。由於吊銬時間長,我和王韋月都昏死過去。我甦醒過來時,一隻手被手銬勒一個大血泡,另一隻手被手銬勒破,身體抽搐、嘔吐,天旋地轉。但是我們對大法堅如磐石,沒有痛苦表情,大度、堅毅、頑強,在那時刻大法的強大威力在我們身上充份體現出。當即惡警張山脫口而出:比江姐還江姐、比劉胡蘭還劉胡蘭,真有佛道神的話還真能修成。我說不了話,但我心裏說:江姐、劉胡蘭怎能與我們大法弟子相比呢!能不能走向合格的佛道神師父說了算。我定定神、慢慢站起來,昂首挺胸自己走回牢房。惡警們眼都直了,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看到他們的心在說:大法弟子真厲害。
在看守所八、九個月的關押迫害中,同修們慢慢悟到:我們是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我們不履行犯人的義務和規矩。排隊打飯時為了不影響犯人就站在犯人後面,不報號就不給我們飯吃。兩天後惡警張山點名問我為甚麼不報號,我堅定、祥和的說:我們不是犯人。無奈給我們打了飯。因為我們同修之間有會背經文的、有會背《洪吟》的,為了多背師父的法,我們把各自背下來的法寫在衛生紙上(看守所的信紙不賣給大法弟子),互相多背法,為了不被惡警們搜走我們的經文,奮力保護,同修們手被鞋底打的黑紫色,衣服被扯壞。特別是副所長惠志江、惡看守雷顯生用皮帶、鞋底毒打我們,把我的頭髮揪去一片,頭和臉都打的腫起來,都變模樣了。有一次搜身惡徒惠志江毒打我時,同屋的女犯都嚇的哭了,可想而知是下了多殘暴的毒手。就這樣我們也堅持煉功,大聲背經文,背的看守所內鴉雀無聲,只有背法聲,再次感到大法威力在人間再現。有的犯人都會背《洪吟》了。
惡警雷顯生邪惡至極,手拿一根皮帶,隨時抽打弟子,最多一次他就打過我二十多個嘴巴,打的鼻子、嘴往出淌血。惡警張玉林(現今已退休,得股骨頭壞死,兒子出車禍腰被壓折),在二零零一年前後也是出了名的惡棍,打罵、吊銬學員他也是極其賣力的,一點善心沒有,所以退休後就遭報應了。副所長惠志江現狀聽知情者說:他自毒打我之後,突然心臟病發作,現在連大聲說話都不能,五臟都有病,非常痛苦。
我記得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那天,由於一個同修看經文時不小心被惡警雷顯生發現,十月七日以惠志江為首十多個看守,把我們全監號的人都圈進浴室,扒光衣服搜查。當時我身上帶一小本大法書,為了保住大法書我拒絕搜身。結果找來七、八個人把我的衣服扯壞,搶走大法書,我跟隨著往回要書,被惠志江拉進值班室,關上門,用皮帶毒打我的頭部,直到打不動了才住手,把我的頭和臉打的老大老大的。我還是向其要書。打我累的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喊:把她拖出去!大法書沒要回來,我和幾個同修當天就絕食要書。
十月八日,惠志江又把我提到審訊室,逼問我書的來源,我不配合他,他就氣急敗壞的拿來皮帶,因為我的頭、臉還腫著,他就打我臀部、腿。我疼痛難忍,這時想起師父的話惡人行惡時,要直視惡人,行惡不停、正念不止。當他的眼光和我眼神碰到一起的一瞬間,他卻顯得孤獨無望,高舉的皮帶一下比一下無力,而且他開始氣喘吁吁臉色鐵青,最後甚麼也不說了,有氣無力的走出審訊室。這時我才看到在審訊室桌旁坐著的另外幾名看守警察頭全都低下去了。停了一會,看守代軍華向我說:遭這麼大罪,吃這麼大苦,圖的是甚麼?我就把師父寫的《強制改變不了人心》第一段背給他們聽,我背完後,他們說:「送回去吧!甚麼也問不出來的。」當我走進號裏時,同修問我:「對你怎麼樣了?」我只是一笑。
十月九日,號子裏的電視正播放武漢大法弟子彭敏和他的母親,實際是遭迫害致死,卻說是撞鐵門自殘不治而死。同屋的女犯問我這不是自殺嗎?當時我真有點激動,把我的褲子脫了下來,大夥一看,有的人立刻捂上臉看不下去了。整個臀部、兩條腿全是青色。有人說:受了這麼重的傷,進門還笑的出來。我說:「這一下你們該知道彭敏是怎麼死的了吧?」我心裏明白,我有師父呵護,我永遠是樂觀的。
十月十三日,惡警又對我野蠻灌食,結果是灌進去就噴出來了。十月十四日我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所裏醫生說生命垂危,通知公安局找到我家,接我丈夫到看守所,丈夫見狀不幹了,對彭明輝等人提出要求:「你們把人害成這樣已經四次了,快死了給人送回家,好點又抓回來,這次好好說道說道,以後愛怎麼煉怎麼煉,永遠不抓她,我就同意你們把她送回去。」公安惡警點頭同意,才給我送回家。
第五次被綁架:遭惡警毒打、電刑、灌不明藥物食
回家後我身體一直不太好,頭昏昏的。可是在二零零三年遷安國保大隊(原政保科)背信自己的允諾於二零零三年陰曆四月十五日,又把我從我弟弟家抓走,說我跟別的學員有來往,硬逼著我說,我不知道的事和我不想說的。彭明輝等人用電棍電了我兩個下午,大脖筋、脖錐、脖子周圍、脖子下面、手指、腳趾、肘關節、膝關節全都電。當時我只覺的頭昏目眩,全身抖顫,心臟偷停,惡警甫永來一把揪住快倒下的我,彭明輝繼續電我,直到沒電了為止。彭明輝等惡警將我送到洗腦班折磨。洗腦班全班人馬都換了,只有最惡毒之人楊玉林還在。惡頭目為了達到其目地,楊玉林帶三個人輪番毒打我,鼻子、嘴鮮血直流,把我打躺在地,揪著頭髮再打,血流一地,頭髮揪掉一撮撮的,直打到三個人再也打不動才停手。這三個惡人打我時他們的臉都變形了,我也被打得血肉模糊。
幾天殘酷的折磨,我身體狀況很不好,由於被抓當天我就對原公安局局長艾文慶及彭明輝鄭重宣布以絕食、絕水為請願條件,要求惡人們無條件釋放我。我的頭脹脹的,一陣陣失去知覺,十多天後小便失禁,不能自理。洗腦班這一期邪惡之徒更是肆無忌憚的殘害大法學員,張口就罵、舉手就打,對我野蠻灌食六次。灌食物時兩個大男人都坐在我的兩條腿上,我聽到有人說:「你倆這麼坐,把她腿坐折了,你倆負責。」兩個人各攥一隻手,一個人揪頭髮,又一個人按胸部,加上遷安市老幹部局的女大夫老張與一名女助手,共八個人對付我一個弱老太太(現今已六十歲)。每次灌食時惡人們八個人也是一身汗,插管有時就用半個多小時,可想而知我得承受多大的魔難。每次灌半盆,肚子灌的鼓鼓的。彭明輝在一旁都說楊玉林:灌的過多,死了你們負責任。可剛灌完就吐出來。最後一次灌食時,還沒等拔灌食管,灌下去的東西全噴了出來,嚇的他們都跑開了。這個張大夫給我輸液我不配合她,她往輸液瓶子裏放不明藥物,我立刻求師父幫忙。
楊玉林、彭明輝等惡人又謀劃把我送開平勞教所,因為有師父有大法保護,也沒達到惡人們的目地,勞教所不收,又把我這個半死半活的人拉了回來。
至今我還不能生活完全自理
回來我記不起幾天後,血壓突然升高、心臟衰竭、兩眼失明、兩耳失聰,這時張大夫著急了,緊急商量怕出人命,這才又把我送回家,正是農曆五月十四,整整二十九天。回家三個月沒會下炕,四十七天沒解過大便,小便失禁。吃不下東西,勉強進點食,就噁心、吐,直到現在走路還頭重腳輕、身體打晃,視力減退恢復不到從前那樣,遠一點就看不清,大小便失禁,還是噁心、吐,頭經常沒有知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靠丈夫幫助。
二零零三年四至五月間,我因被惡警強烈揪打、電棍電,頭髮幾乎掉光了,後來又長出來了,但那些殘發還保存著,灌食時別掉的兩顆牙已丟掉了。有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至八日我被惡人惠志江毒打後,於十月二十六日照下幾張照片為證據。
剛到家時我不會坐著,感覺尾骨如同裂開似的劇痛,叫家人把我送遷安人民醫院做個鑑定,家裏人膽小不敢,我自己又不能動彈,像也不敢照,怕我好點後給別人,怕招來麻煩。在被打的二十天後,我一再請求家人,才照了這幾張,照時傷勢好的快差不多了,都不疼了,還那樣子呢,可惜沒有留下當時真正的慘狀。
以上是我個人被迫害的一些情況。在這裏正告那些為江氏集團賣命的邪惡之徒:你們的所做所為神和人都看在眼裏了,如不立即停止對大法弟子的迫害並挽回對大法的犯罪,神開始清算時你的所做就是你的加倍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