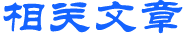在流離失所中證實法、救度眾生
在流離失所中證實大法救度眾生
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修煉前我身體有多種疾病,修煉後我全身無病身體健康。道德回升家庭和睦。日子過的越來越好,有個家庭各方面條件也比較好的環境,雖然比上不足比下還是有餘,家中布置的很溫馨,本來可以過著舒適無憂無慮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我遭邪惡迫害,被迫遠離家鄉,輾轉來到一個城市。這裏的一位協調人(下稱B)與另一同修將我安置在一位單身女同修(下稱A)的家中。這位同修三十歲左右的樣子,交流中才知道,她母親被迫害死了。她遭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每日鬱鬱寡歡。她一人獨居,住所非常簡陋,連衛生間都沒有,這一切對過慣優越生活的我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我心想不論怎麼樣,這也是修煉,為了救度世人,為了能證實大法,甚麼苦也不是苦了,想起監獄裏被邪惡迫害的同修,這點苦算不了甚麼,得了大法我有師父,比甚麼都幸福。我也不斷找自己修正自己,在法中歸正自己,去除執著。
雖然在流離中,生活來源也沒問題,身上帶著一張銀行卡,從裏取出一萬元錢。後來師父借一同修的嘴點化讓我不要去銀行取錢了,我明白邪惡為了迫害好人甚麼壞招都會使出來的。中途回了一兩次家,得到我放在家中的幾萬元錢,這足以讓我生活幾年了,感謝師父!
在師父的安排下,我們這開了一朵小花,供這地區的同修救度眾生。我負責下載打印,A負責裝袋,我有時間也一起裝袋,有時候忙不過來,B會找幾個同修一起裝袋。下午幹完活,我們倆就學法。一位大姐叫起我們一起晨煉。因為我剛得法迫害就開始了,所以還沒享受幾天集體煉功,環境就被中共破壞掉了。在家中我自己一直不能起這麼早煉功,三點多起床對我來說太困難了,別的執著我覺的還好去,這個起早我感覺是最痛苦的事了。在這位大姐的督促下,我必須起來,也不好意思不起來,她一敲窗子,我一骨碌就爬起來,接著叫醒A.小集體晨煉感受真好,一整天身體都感覺很輕鬆,精神飽滿,感受大法的超常,美妙。
同A生活了近半年,在一起熟悉了,也有一些小摩擦,她生活散漫,她說我有潔癖,我說她太邋遢,面板、面盆結了厚厚的麵粉,也不知道多長時間沒清洗了,面板周圍都是菜葉,有的都發黑了;早上起床後她手也不洗就揉面,口中叫著:「姐,我們今天吃花捲。」哎,看到她熱情的臉龐覺的也好可愛,也就不說甚麼了。後來我默默的把廚房收拾乾淨。她經常在我耳邊說一些翻來覆去的話,我理解她是受了精神刺激,內心的痛苦。後來從別的同修那知道她受了強大的精神壓力後是帶修不修的狀態。在邪惡的迫害下,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家庭,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兒女,又有多少大法弟子的小孩子失去父母無依無靠。
這裏原來是學法點,人來人往的都知道,有鄉鎮人員來查A的住所。為了安全,B在其他同修的資助下又幫資料點租了一套房子,同時供我居住,這樣就兩全其美了。非常感謝師父的安排與同修的付出,不過我還是想以後將租房錢還給他們。
我搬進來才發現,房間太大,足有160多平米,一來我覺的有些浪費,二是離B家太近,在一個小區,他的妻子是常人,會不會哪天發現了產生誤會(後來意識到這個想法就把這事給定下來了),三是我有點恐黑,而且B說為了安全這裏晚上不要開燈,就讓別人以為這裏沒人住。這可真是難為我了,開始幾乎一到晚上就呆不踏實,說實在的,晚上一人住有些怕。後來想:我怕甚麼呢?師父就在我身邊呀。這樣一想也就沒事了。晚上不讓開燈,到冬天的時候不到傍晚六點天就黑了,怎麼做飯吃飯呢?算了,那就只吃兩頓飯吧,晚飯不吃了,節省時間還減肥。但是晚上因為要學法,不開燈怎麼行?還有好多事要做呀。後來想了一個辦法,買了一大塊遮光布,往臥室窗子上一掛,還真管事。晚上我就在臥室裏學法、上電腦看明慧網等等。
我幾次對B說,幫我找一個女同修來一起住。但他不想讓A與其他同修知道我在這,覺的這樣更安全。他讓我放下找個伴的執著。我只能聽從他的安排。他還讓我出門不要讓別人看到我,尤其是不要讓他的妻子看到。我幾乎一週出去一次購買必要的生活用品與蔬菜,每次出門都很緊張,有時候覺的心裏很苦,感覺像是在防賊一樣,進出門也很小心。有一次我心裏苦,就有些埋怨:住這麼近怎麼能不讓你妻子知道呢?你就不能堂堂正正把我介紹給你妻子嗎?拎著剛購買回來的物品,正這樣想著,忽然有甚麼東西在閃,我一轉頭,發現是師父法像周邊的光環在閃動,我心裏一激動,趕緊跪倒在師父法像前,淚流滿面的對師父說:「師父啊,弟子真是愧對師父的慈悲苦度,這哪叫甚麼苦呀,謝謝師父!弟子知錯了,謝謝師父看護!」
這個資料點不只供應當地的同修救人用,還要供應外縣的同修,有兩台大的、幾台小的打印機供我使用。每天六點發完正念,我就打開機器開始打印,B也時不時的來幫著裁切。開始時主要打印《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正常時一天能出幾十到一百多本書,後來美國大選時又打印一些應時的小冊子,整天忙忙碌碌,有時候我就想,我就像專修弟子一樣,全身心投入到救度眾生證實法的事情中,心裏真的感覺很幸福、很充實。
有一次,外縣協調同修去別的地方順路來拿貨。一般是B送到一個地方再轉給她分配,今天她順路就來了。她一看到我這存了好多箱資料,滿床都堆著資料,就提醒B與我說:「不要存這麼多資料,這樣不安全,把這些都轉走吧。」我們也都接受同修的提醒,畢竟現在還處在邪惡迫害時期,安全不容忽視。但我想,這些資料在另外空間都是閃閃發光的生命,對清除邪惡有巨大作用,而且有時等同修需要了再做來不及,耽誤救度眾生,所以一般我這都有存貨。我就發了一念:請師父加持,這些資料多了也安全。
購買紙張耗材時,更是要多加注意,先發正念,等卸車時,都是B一人往裏拿物品,他非常快速的往屋搬,十幾箱紙,有時二十箱,他兩箱一趟往屋裏運,這樣也得來回幾次,還好資料點在一樓,B怕我暴露,所以我在屋內接應,開關門。幾年裏,在師父的看護下,每次進貨幾乎都沒碰到過人,就算有驚也無險,順利的走過了那幾年證實法的路。在此感謝師父看護!也感謝那裏幫助過我的所有同修們!
純純淨淨救度世人
開始做大法書。因需要裁切,需求量也比較大,資料點一個人忙不過來,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同修來配合,B同修就經常來,一來二去,感覺男女單獨這樣相處不太適合,我給他提出來,讓他儘量少來,沒事就別來了。他也考慮找一個女同修來幫忙,可這地區同修很少,有一女同修在這附近,可是她帶孫子,還有生意在忙,也沒有那麼多時間來做,裁切也得有點力氣。這事就擱置了。
由於跟B家住的太近,終於有一天他的妻子發現了,他說的有事是到我這裏來,在不了解事情經過的情況下,產生了誤會,跟他大鬧了一場。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雖然我比這位B同修年齡大兩歲,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由於修煉後,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所以他妻子以為他金屋藏嬌,因為他當常人時就讓他妻子不放心過。我心想:這樣有損大法弟子的聲譽,好在他妻子是明白真相的,但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妒嫉心上來,真的甚麼事都能幹的出來。後來B同修忍不住對我說了,他妻子揚言要舉報我。我心生一念:心正不怕影子歪,我有師父看護,誰也動不了!當時也想到要離開這裏,一是暫時沒有合適的地方,二是看到滿屋的資料,責任心又佔了上風,感覺使命還沒有完成。後來我找了個機緣,找到他的妻子跟她解釋,並再次給她講明真相,邀請她來我的住所,可以隨時來,並說:「大法修煉,我們書中要求我們很嚴,我們連一思一念都要修善,都不能動念,你放心吧。」她算是個能通情達理的人,以後就沒再鬧了。過年時還把我叫到他們家過年,我也是象徵性的去了一會兒,就回自己住所,我不想給別人再添麻煩。他妻子後來幫他望風,看看小區有沒有可疑的車輛、閒雜人,陪他去送貨等等,做了好多好事。
修煉沒有偶然的事,自上面事情發生後,我找自己,看自己的內心,覺的可能還有好多沒意識到的執著、色慾等干擾,有些不好的因素沒去乾淨,空間場不純淨,被邪惡鑽了空子。還有B同修的一些因素,就是他還沒意識到有些不好因素會左右他,這些後來在一位學法不長時間的大姐身上表現的很明顯,他還沒修出能分辨清楚真我的能力。
有一天,當地同修聯繫上我,帶來一個也是流離失所的大姐,問我這裏能接納她嗎?我非常高興,早就想找一位女同修一起做證實大法的事。因當時沒法聯繫B,就沒有跟他商量把這位大姐留下來了,心想B也不會反對的。果然B也很熱情的互相做了介紹,從法理上交流了一會,隨後我把大姐安頓好了,她缺少甚麼我這都有。
可沒想到接下來的場景,讓我感到再留大姐在這下去,就會有大麻煩事發生。我喜歡靜,因為做資料這幾年,在師父的看護下,讓我養成了謹慎、理智的對待一些身邊的事,也注意用法來衡量,不容易被一些不好的因素鑽空子,更是特別注意男女有別。尤其跟這位B同修相處做事,都是嚴格的要求自己,阻止了一些不在法上的事發生。而這位大姐是新得法的,她來到我這沒幾天,就把一個我用了幾年的菜籃子搞的稀巴爛,拖布頭也搞掉了,一隻碗也打碎了……我想:萬物皆有靈,這是在提醒甚麼呢?我提醒她小心一點,她說:「我要不搞衛生這些東西也壞不了……」她喜歡熱鬧,經常做一些吃的來招待B或者送食物給B,說話也輕浮,有一次蒸了些紅豆包送給B六個,結果讓B的妻子給扔到垃圾桶。
我幾次找大姐交流,說我們倆生活就好了,不要留B在這吃飯,我希望我們能純純淨淨的做事,不要摻進來不好的因素。最讓我擔心的是,晚上她在客廳的黑屋子裏呆著,說是要做事。我跟她說:白天做事,晚上跟我一起學法吧,因為就只有我這屋子晚上可以開燈,其它房間沒有安裝遮光布,也沒必要安裝。但我發現,那個B每天有事沒事都找她來弄這弄那,兩人在飯廳一間黑屋子裏,偶爾的可以理解,天天來就特別了。而且那個大姐也不會弄電腦甚麼的呀,可B就是來找她弄。大姐不會弄,等B走了後就來問我怎麼弄,我告訴她怎麼怎麼弄好了。幾次下來,我對大姐說:「等晚上他再來時你把他叫到我這屋裏來,我有事要找他。」晚上B準時來了,我請他們坐下,我說:「我這人說話比較直,咱們都是修煉人,走到現在也很不容易,現在我與大姐是這種處境,更要修好自己,不能讓邪惡再鑽空子了,你這幾乎每天晚上在那黑屋子裏有甚麼事要說嗎?再說大姐也不會甚麼電腦技術甚麼的呀,你找她弄甚麼呢?」他低頭一聲不發。我對大姐說:「你有啥事先對我說,別沒事就麻煩協調人,他也很忙,我解決不了你再找他也行啊。」她也沒話可說。可是接下來還是不行。
我先從我這找自己看有哪顆心沒去乾淨,有沒有妒嫉心?好像沒有,因為這位大姐沒有甚麼可讓我妒嫉的,她沒有甚麼技能,長的又矮又難看,黨文化重,說話大聲沒有女人味,再說,由於我跟B對法的理解及理念上有好多地方不合,我一直拒B於千里,他表示出來的人心,我會心生厭惡,有時候他太囉嗦,我會阻止併發脾氣(魔性要修去),現在想想曾傷害他很多次。我是很感激他對我的幫助,其實B這位同修哪都讓我佩服,在疫情期間更是關照我,幫助我很多,沒有他的幫助我是走不過那個時期,比如小區封鎖,我沒有身份證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他進出小區幫我購買這購買那的,甚至幫我往外扔垃圾。現在看來把我安排在他住的同一小區還真是師父的慈悲看護。這個住所哪裏有要維修的,他是有求必應。他對其他同修都是這樣,誰家有事都找他,這地區由於同修少,只有他一位協調人,所以那時候,覺的在我這種情況下他能這麼幫我真是難能可貴。可是感激不代表甚麼都要聽從,不在法上的我也不能看到不說,用人心人情去維護也不對呀。
這位大姐幾乎每次發正念時,一秒也立不起來掌,提醒她,一秒不到又倒了,頭也垂到胸口睡著了。跟她交流:你這發正念經常這樣不行啊,空間場清理不乾淨也會有各種干擾的。她說:「誰沒倒過掌,你沒倒過掌嗎?」我說:「好好,我也有倒掌的時候。」一次,她在夜晚發出淒慘大叫,把我嚇一大跳,跑去一看,沒燈也看不清楚,但從她說話的聲音可以聽出,她受了很大的驚嚇,我問怎麼了?她說有一個黑衣人從窗外要撲向她,她嚇醒了。還有一次她說:夢中看到好多蟲子,滿房頂都是,大大小小的。她也說:是我這空間場不乾淨。我說:那多發正念吧,清理乾淨。接下來她又鬧著要出去講真相,原來她是面對面講,讓B給她找個地方住,要出去講真相。B也給她找了A的地方,她去了一看當晚就回來了。可是她在這種需要安靜、不自由、像沒住人的環境中是呆不了。有一次我也是沒忍住,對她發了脾氣。當時我很奇怪自己,因為我是個很溫柔的女性,從沒對別人大聲說過話,可是在這卻暴露出這麼大的魔性,這也是我要清理乾淨修去的。
她一直吵著要出去講真相,不願意在這裏被束縛。我一直可憐她與我一樣是流離失所的,一直想留下她。這時聽到一個聲音說:「你為甚麼要留下她?她自己都吵著要走。」我想也是啊,為甚麼留她呢,在這裏破壞著資料點的安靜,還有她這樣不理智,這樣下去這裏也不安全了。我就對她說:「那我幫你聯繫送你來的同修找個更合適的地方吧。」沒想到她不假思索地說好。我通過一個常人聯繫上當地送她來的同修,給她找到一個單身女同修的家,把她送走了。她在我這待了近三個月。送她走這事我也審視了自己的內心,是不是真正為別人著想,目前看來她離開是最好,否則要出大亂子。她在那個新學員家一起學法是最好的,多學法提高的快,而且那個環境比我這要好的多。可是聽說她到那個新學員家要人家三千保姆費,那個新學員生氣,第二次腦出血住院了。這個大姐在那也住不了了。哎,修煉是何等嚴肅啊,一思一念,真是不實修就是在堵自己的修煉路。
後來不長時間,我也因別的原因離開了這裏,我想師父給我安排了一個更好的去處。
從個人修煉思維的框框中走出來
通過學法不斷深入,師父把法理也點化給我,我也有了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應該怎麼做的粗淺認識。有次去鄰縣送修好的打印機,順便看看那的同修。正好到中午吃飯時間,那的協調同修就安排我們在她家吃飯,還叫來了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聽說這位大法弟子有些固執,誰說甚麼他不太聽,總認為自己做的好。吃完飯我們簡單交流,開始我只是聽,後來聽到他說:「村裏左鄰右舍都知道我是個好人,妻子在家癱瘓十年了去年剛走,這十年都是我一人照顧的,孩子們回來我也不讓他們照顧,怕他們照顧不好,為了讓老伴多活幾年,這十年我一人細心照顧,做好人嘛。」我聽了後覺的應該把我不同的想法跟他交流一下,我說:「假如這是個人修煉時期,您做的太好了。可是現在是正法時期,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還得去救度眾生,這麼多眾生面臨末劫,假如不明白真相,將有被淘汰生命的危險,這十年你只為一個人做個好人,而耽誤救度多少眾生啊,還有你這是剝奪了你的兒女盡孝心的義務呀,再說,人的生命是有定數的,不是我們人為的就能延長來的,這是我自己的一點體悟。」他聽後一聲不吭,像在思考甚麼。
還有一次,B來這裏送東西,遇到一位同修,我們一起交流舉報那些還在繼續幹壞事、助紂為虐的壞人惡警,B說:「警察把我綁架到公安局時,對我很好,對我也很客氣,也沒罵我、打我。」我聽出他的意思,對他說:「你這樣一說讓我想起了一個故事,北歐國家瑞典的首都叫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的職員被幾個綁匪綁架做人質,後來警察抓住了綁匪,解救了職員,有幾個職員說:把他們放了吧。他們對我們很好,還給我們飯吃,有個女士還要嫁給一個綁匪。」我簡單的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由來講給了他聽,他也略有所思。警察應該去管壞人,而不是抓好人。他們背後有中共邪靈,在那些不好生命的操控下,警察表現的越來越猖獗,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在不斷升級,甚至很殘酷,他們都在不自覺的參與其中,那麼這個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所犯下的罪業,他們人人都有份。
我發現還有好多同修陷入家庭的羈絆中走不出來,家務事、兒孫事,拖的他們學法沒時間,救人就更走不出去,慢慢走了舊勢力安排的路了。有的同修說我,流離失所也是在走舊勢力安排的路。我在想,這次流離,是我沒修好,還有人心被鑽了空子;也可能是師父的安排,將計就計把我從繁雜的家務中解脫出來做三件事,還有別的可能,我們在迷中不知道有些事的因緣,但我覺的我決不是在走舊勢力安排的路,舊勢力安排我當時是關監獄,而師父解救了我。再次感恩師尊慈悲看護弟子。
有同修勸我回去面對,這時一段師父的講法在我腦中迴盪,當弟子問「上了邪黨黑名單的海外弟子多年回不成中國了,現在回國探親、證實法時機成熟了嗎?」師父說:「現在先別回去。你在它的黑名單上,它要迫害你。它即使不迫害你,它也會用各種拉攏的手段對付你,儘量少找那個麻煩。既然你們在這裏證實法,那這就是你修煉的地方。其實叫你回去的因素也可能是對人心的檢驗,因為修煉才是你的路。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學員在做呢,你放心,他們一定會做好的,我是有信心。」(《洛杉磯市法會講法》)
我當時離開家也沒多想,那也不是偶然的。思維中還有許多意識不到的執著容易被邪惡鑽空子,我還在邪惡的黑名單上;再說回家也沒有現在全身心的證實法更好。現在在這能做三件事,而且是全身心的投入,只要能救度眾生,那就是師父給我安排的路,師父無所不能,只要我走的正,師父會將計就計的給我安排我所要走的證實法的路。而且,回去也沒我的位置了,家已不像個家了,這幾年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家人已承受不了,打電話也不接,外面還有人,房子也被他的家人住著,我回去也沒地方呆了。第一次回家他接待了我,給我做了一大堆好吃的,我拿到了我放在家的幾萬元錢,第二次回家,他一分鐘沒讓我待就把我趕了出來,並說給我半年時間,不然我走我的陽關道,他走他的獨木橋。出門時我看到客廳門上插著的女式拖鞋……
有人說你再找一個,也曾遇到有同修想再組織家庭的。我想:都啥時候了。為了救家人,為了救眾生,我不想也不能走那一步。我一直在想著救家人,每次一有機會就講。有的明白,有的想學,有的雖然現在不理解,總有一天會理解的,他們也是怕,在邪惡的高壓下,他們承受了許多苦難,想起我被非法關押在黑窩的時候,丈夫連夜開著十多個小時的車去監獄探望,冰天雪地也不間斷,一個常人能做到這一步是很可貴的。現在是社會風氣無神論的教育,整個大的環境對家人的污染,人都在其中誰也抵擋不了,隨波逐流的往下滑著,使他們也造了不少業,只有修煉的人才能使道德各方面都得以昇華。作為大法弟子不能記前嫌,就想著救他們,給他們一線希望,哪怕最後他們負了我們,我們也不能放棄對他們的救度。因為我知道這一世他們等待了千年,吃盡了苦頭。
對救眾生不利的事想也不要想,我也邁不出這一步,現在救人時間很緊,哪有時間考慮這些,有人說找個修煉人共同精進。但我也看到,有好多同修家庭矛盾重重。層次不一樣,對法的理解不一樣,在一起難免有許多磕磕絆絆,並不是想像的那樣理想化在互相促進。
層次所限,這是在現有層次的一點體悟,不當之處望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師尊的慈悲看護!
(責任編輯:文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