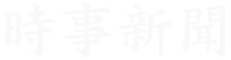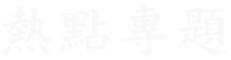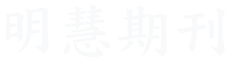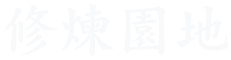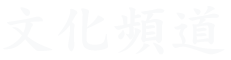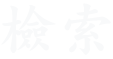到郵局、公安局講真相 在營救同修中證實法
一、到郵局、公安局講真相
訴江大潮剛開始的時候,同修們認識到應該寫訴狀,而且要快。一部份訴江的同修陸續接到了回執,而稍微拖延了幾天的,就不太順利。
有一天早上我在吃飯,一位鄰村的同修來了。她說自己寫的訴江狀被扣了。我們經過交流,決定按照法中的要求去做,哪裏出現了問題,就是需要我們去哪裏講清真相。於是,我又叫上了幾個同修去了郵局。
當時我們沒找到局長,就和職員們講真相,告訴他們:我們是無辜被迫害的;郵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信件是違法的,將來要承擔法律責任。他們說做不了主,讓我們找局長。
一連幾天,我們都去郵局講真相。在這個過程中,有人真正明白了真相,偷偷的告訴我們局長不是當地人,告訴我們他是甚麼地方的口音,在幾樓上班。我們就去找局長,開始局長迴避我們。
又過了幾天,我獨自一人又去了局長辦公室。門開著,有七、八個人圍坐在一個長桌邊,好像在開會。看我突然出現在門口,有一個異地口音的人說:「你找誰?」我說:「找局長。」他說:「局長不在。」我笑了笑說:「當局長應該是很光榮的事,怎麼你不敢承認?」他也笑了。
我說:「你就是局長。」他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我怎麼知道的不重要,我今天找你問你幾個問題。他說:「問吧。」我說,郵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通信信件,是不是違法?他說:「是。」我說,國家領導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無故殺人,是不是犯罪?應不應該把它告上法庭?他說:「應該。」
他問我:「大姨,你是煉法輪功的?」我點點頭:「是。」他讓我坐下。我給他們講了「天安門自焚」偽案、傅怡彬殺人案等真相,一講就講了半個小時左右。他們一直在靜靜的聽著,沒有人插話,也沒人打斷我。
我問他們有甚麼不明白的?局長說,我告訴你實情吧,我個人真的沒有權力扣押你們的訴狀信件,是公安局來人要求我們這樣做的。你去找他們,也給他們講講吧。如果他們說可以給你們寄,我們沒問題。他站起來,我看到他的目光充滿同情,他好像明白了。
他讓我去公安局,而我猶豫著:去不去呢? 去吧,有人心障礙我,覺的有壓力。可是我又明白,這是師父的安排,是師父安排我在講真相救人中放下為私為我的人心。我想走師父安排的路,要衝破人心的障礙,徹底否定舊勢力的一切安排。
我獨自騎電動車來到公安局門口,看到那些出出進進的警察,心裏還是有點不穩,我感覺到怕的物質向我襲來,我立刻抓住它:怕心不是我!我不要你!我今天就是來救人的。我請求師父加持我。不到一秒鐘,怕心頓失。我感到自己被強大的正能量包圍著,我好高大。再看那些警察,很小很小。
我大大方方的走進了公安局大廳,做了實名登記。登記的人問我找誰?我說找政保股股長。他問我甚麼事?我就藉機給他講真相:江澤民如何栽贓陷害法輪功,如何編造謊言迫害無辜,迫害死無數法輪功學員……我們要控告他是合法的,可某某某命令郵局扣押我們的信件,所以我要找某某某。他很客氣的親自把我送到某某某的辦公室門口。
我看見某某某和另外三個警察在說話,我站在門口微笑著看著他們。某某某說:「你找誰?」我說:「找某某某。」他說:「你認識他嗎?」我說:「認識,就是你。」他問我:「你是誰?」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
他問:「你有甚麼事?」我說我問你幾個問題:第一,中央領導利用權力殺害無辜,編造謊言栽贓陷害,算不算犯罪?他說:「算。」第二,作為合法公民,有沒有控告他的權力?他說:「有。」第三,扣押我們的信件違法不?他說:「違法。」
我說,那你為甚麼要郵局扣押我們的信件?他說:「我沒有扣押。」我說,那麻煩你和我去一趟郵局說明情況吧。他說:「我不去。」我說,我有局長的電話,你給打個電話可以吧?他說:「不打。」
他說,我可以給你指條路,你去告他們吧。我問:「在哪告?」他說:「到法院。」我說:「那我就連你一起告。」他說:「你告我幹甚麼?」我說,就你現在的職業,你能說沒有參與過迫害法輪功學員?我現在誰都不告,就告江澤民。因為我們都是受害者。你想想,你聽信謊言的欺騙,執行了錯誤的命令,將來要償還的,你不同樣是受害者嗎?!現在就在給人醒悟的機會,你可得聽進善心相勸啊!
他問我:「還有事嗎?」我說有,我想你一定是黨員吧。他說:「是,不過我退了。」我問誰給退的?他說:「你別問了。」我說,你既然退了,那就說明你知道邪黨不好,對嗎?他說:「是。」
我們整個的談話過程非常和諧,互相尊重,好像是和朋友在交談。旁邊的三個警察還和我互動,配合我講真相。講了很長時間,最後他說:「沒事了,你先走吧,我還有事。」我說:「好的,不耽誤你時間了。」
從公安局出來,我身體輕飄飄的。我和警察之間,沒有了迫害與被迫害的概念,是救度與被救度的關係了。擺在我面前的生命,不分階層、職位高低、貧富,都是我要救度的對像。他們需要我們,等待我們用從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救度。
從那以後,我都是面對面講真相。出現人心障礙,我就立刻清除並求師父加持。有時遇到不理解的人或者誤解很深的人,我都不會被帶動,我深知他們是因受謊言迷惑太深,如果我不能把真相給他們講清,他們就很危險。
這時我想到的是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責任,就需要我發揮在大法中修出的寬容、理解、忍耐力、吃苦能力、善心、責任心。有時碰到這樣的人,很需要時間我也決不放過他。當我真的講通了,我感覺這才是在講真相救人。是我的心符合了法的要求,我的心裏才會踏實坦蕩。
二、在營救同修中證實法
二零一九年,鄰縣的一位同修被迫害,她的女兒小敬(化名)通過其他同修找到了我。小敬不修煉,但是了解真相。她主動要求我幫助她,她說她們本地的同修很少。她已經花了一萬五千元請了律師,打算做有罪辯護,只想儘量少判。
我給她講真相,我說我和你母親是同修,同修一部大法,法輪大法是正法。我們做無罪辯護為的是揭露邪惡對大法的誣陷、造謠,為的是講真相救人。你母親的事就是我的事,這是大法弟子的責任。
小敬說想辭掉那位律師,她說她看那位律師也沒能力,我又不會給他講真相,但是錢已經給了人家。我看到小敬此時的心態已經在變化了,她沒有考慮錢,而是想怎樣證明母親是無罪的。我和她說好了明天去見那位律師。
第二天,我帶了真相資料和真相U盤,打車到了律師事務所(我家距離那一百八十里地)。我給那位律師講了真相,講了一切罪名都是強加的,都沒有法律依據。講了將近一個小時的真相。
我問他:「你能不能為我們做無罪辯護?」他說:「我還沒接過這樣的案子,就算是第一次做無罪辯護吧。」我把真相資料U盤給了他,告訴他多多的了解一下,對這個案子有很大的幫助。他說:「好,我好好看一下。」我告訴他:「我相信你一定能行。」這位律師已經開始明白真相了。
我們順利的辦好了家屬辯護的許可。我對律師說,我們各自寫辯護詞,寫完後我們互相交換著看一下。律師答應了。一個多月後,非法開庭的日子定了。我把辯護詞給了小敬,讓她熟悉一下,因為第二天上午九點就開庭了。
小敬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開車到我家。我問她:「辯護詞熟悉了吧?」她說:「我有改動。」我接過來一看,她把我認為最關鍵的、在法庭上堂堂正正講真相的部份刪除了。比如:邪惡利用《刑法》第三百條誣陷法輪功學員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罪。我是這樣寫的:她是一個平民百姓,她有何能力破壞國家法律實施?說她犯罪,她傷害的又是誰?必需說清楚,否則,就是強加罪名,那麼真正犯罪的又是誰呢?!
我理解小敬的心情,我對她說,咱花錢,不就是要證明我們沒有罪嗎?你也知道我們修的是正法正道。所有對法輪功迫害的藉口都是強加的罪名,我們是絕不能承認的。我想你母親讓你聘請律師,應該也是這個意思。你不要擔心,咱就做咱該做的,就是裏應外合營救母親了。我問她:你是不是希望母親更堅定?她說:「是,姨,那就還按你的意思吧。」
我看時間真的不多了,就求師父幫助,不能錯過講真相證實法的機會。把辯護詞修改後,再打印出來,檢查了一下,她又念了一遍,沒有了誤差。她說:「怎麼現在我沒了怕、沒了擔心呢?」我說,因為你明白了我們修的是正法,沒有罪,是公檢法人員在犯罪。我們今天做的越正,才是對他們的挽救。她笑了。
我們到了法院門口,本地同修們已經在配合發正念了。有的進了法院旁聽,有的在法院外。律師也已經等候在那了。小敬的哥哥和她的父親都進了法院等候。看到我們和律師打招呼,小敬父親趕到律師面前(小敬請律師的事沒告訴她父親,他不理解大法,受謊言迷惑很深),大聲嚇唬律師:「你不能做無罪辯護,我要你做有罪辯護。」律師和他解釋不清,小敬父親大吵大鬧。
我趕緊問了小敬父親的名字,告訴同修們叫著他的名字,清除他背後的邪惡因素。我又把小敬父親叫出來,單獨給他講真相,並告訴他:「別站錯了隊,幫助邪惡迫害自己家人。」他好像明白了,冷靜下來,不鬧騰了。我告訴律師不要受他的影響,把我們要做的做好就是了。
在法庭上,小敬為母親做了無罪辯護。她表現的端莊、沉穩,柔和的聲音透著剛強、堅定。每句話都啟迪著在場每個人的良知、善念。律師的辯護詞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我看到庭長抬起頭,眼睛盯著我們的辯護人,可能他聽著有些刺耳,但是他沒有打斷辯護人的辯護。小敬的母親也正念的做了自我辯護。我感覺那次開庭真的是震懾了邪惡,所有參與的人員沒了囂張的氣燄,蔫蔫的。
開庭之後的幾天,我想找機會再給庭長講真相。我讓小敬撥通了他的電話,小敬說:「能不能讓我們進去,有事問您。」他說:「別來了,你們寫的辯護詞那麼擋勁(方言,意思是我們的話很有力度)。」
聽說後來有鄰縣同修的非法庭審又要在我縣開庭,這個庭長不幹了:「為甚麼不在你們縣開庭?你們怕遭報應,我也怕。」
後來,我陪小敬回老家去看望她的父親,一是安慰,二是把沒講清的真相講清,為小敬母親開創較寬鬆的環境。我想每個同修的事都是我的事,我要多關心他們,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個人體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請同修慈悲指正。
謝謝師父!
謝謝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