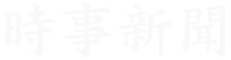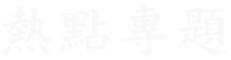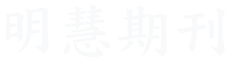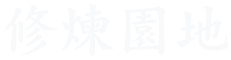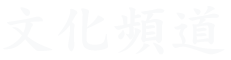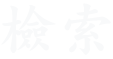突破觀念 疫情救度眾生
我們這偌大的一個小區,也只留一個進出口,片警、居委會、物業和保安公司聯合守衛,每班六、七個人,二十四小時輪流值勤。每家發一張通行證,兩天只允許一人次出去採購食品,回來還測體溫實名登記,晚上七點半以後基本上就不讓出門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就像一記猛錘,狠狠的敲醒了不精進的我,使我意識到舊勢力淘汰眾生的劫難已到,同時也悟到這正是我們這些不精進的弟子們彌補過錯,抓緊時間救度眾生的一次好機會,我不能再吊兒郎當的懈怠了。
我家是資料點,十幾年來我一直供應著同修們的真相資料。過年期間,我照常準備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年後給同修們送去。這突然的半封閉,打亂了我們救度眾生的安排。我現在供應的幾位同修,大都是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一位過年去女兒家被堵在那裏回不來了,一位不知甚麼原因,在約定的時間地點沒來取資料,因沒有她的電話也無法聯繫。另一位是經商的同修,家不在市區,我不知他家地址,他是不定期來我這裏取資料,不過,除我這他還有另外的供應渠道。只有一位同修我們還能正常的來往。另一位就是我八十五歲的老母親了,她與我住在一起,只能在本小區做了。
在這期間師父又給我安排了一位很精進的同修。平時他在別處取資料,因疫情斷了資料的來源,他來我這裏取了。因突然疫情,打印好的資料暫時不適合當前的形勢,先放一放了。當時明慧相關的成品資料還沒出來,我就自己排版編輯了明慧網有關疫情和九字真言小故事的小冊子,用明慧網的平安卡片作封皮,又設計了幾個精美的封皮,及時的打印出來大面積散發。後來明慧的資料出來後我就大量的做明慧的資料了。
一、突破家庭關
我是單親家庭,在女兒少年時我曾被中共綁架,在黑窩裏被迫害關押了半年。這給孩子心靈中造成的創傷是很大的。她雖然聽過法,但沒有真正走入修煉,不過很支持我修煉,也從未阻礙過我救度眾生,並且還常替我傳遞資料。但我每次出門講真相她都會提心吊膽,生怕我出事(是我安逸心太重,太懈怠造成的),直到平安到家她才放心。這次疫情出現了,我要出去救人,她卻阻擋了。當然她不會擔心我染疫,她知道煉功人不會得病。她所擔心的是共產黨現在已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外面沒有行人,到處是維穩的便衣警察。她怕的是我修煉狀態不好,會出事。要我在家好好學法調整好了再出去。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調整應該是在救度眾生,做好三件事中提高上來,而不是閉門在家學法。我理解她,所以也不去與她爭,就默默發正念:解體阻礙我救度眾生的一切邪惡因素。這樣本來她想貯存食物要佔用出門的機會由於種種原因取消了,絕大多數出門的機會都留給了我去救人。
二、對攝像頭的認識
走出家門,我首先要突破的關就是攝像頭的問題。一開始我對攝像頭的監控是沒有概念的。後來同修們談論的多了,又加上馬路上、小區裏大量的裝了攝像頭,並且我樓下的攝像頭正對著我門口,派出所警察也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偷偷對我錄了像。我漸漸的對攝像頭產生了戒備心,發資料時儘量避開攝像頭。現在疫情來了,小區進不去了,路上行人也戴著口罩行色匆匆。怕染疫,根本不敢跟陌生人說話。我看到馬路邊上停放的一輛輛私家車。無論是市區的主幹道的輔道(自行車道)上,還是通向各小區的小馬路上,到處都停滿了私家車,侵佔了自行車道的一半位置。而無論輔道還是小馬路上也到處都裝滿了攝像頭,二、三十米就有一個。有的地方正反兩個方向都有。
我決定在路邊的汽車上投放真相資料。因為在疫情期間行人很少,連拾荒者也被封在家裏了。我發的資料幾乎都是關於疫情的大冊子,封皮都用彩噴紙與雙面銅版紙製作,用透明塑料袋密封好,大多數正面朝上放在車擋風玻璃上,精美漂亮,又是有關疫情的,人都應該感興趣。
關於攝像頭師尊講過:「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產品在全世界人們心目中是最糟糕的,是不是?我聽說那攝像頭,安上去一千個,五百個都不好使,(眾笑、鼓掌)剛把那個弄好了,那邊又壞了。它那個質量,它那些東西,再加上人浮於事,反正中共邪黨幹甚麼事都是糗事」[1]。師父還告訴我們:「沒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2]
從另一個角度講,攝像頭是由人類這一層物質空間的分子構成的,而我們修煉人的身體分子成份將由另外空間採集的高能量物質代替,人的東西怎麼能對神起作用呢?並且師父的法講的這麼明,我再對攝像頭顧慮其實就是不想褪去人的殼,走向神。是在我骨子裏還有不信師不信法的因素,這正是我要清除的。法理上雖然明白了,但在馬路的主幹道的輔路上投放資料時(那裏攝像頭非常密集),我的思想業還是時不時的冒出來,我就不停的發正念排斥它,消滅它。往往都是在家裏想著去哪發資料時有怕心,不願去。但只要我堅定的走出門去發,就正念越來越足,最後就像入無人之境,無論身邊有沒有人經過或看見也都很坦然。但也不都是每次都這樣。
有一次,我在通往一個小區的路上發資料,不知何故,突然心中一陣恐懼襲來,怕的因素竟然讓我產生從未有過的緊張感。按照過去慣例,我會立刻停做,回家發正念。但此刻我沒有被此狀況所動:我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立刻不停的發正念,但腳步卻沒有絲毫的停頓。我背著師父的法:「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惡就垮 修煉人 裝著法 發正念 爛鬼炸 神在世 證實法」[3]。「講真相救度眾生,舊勢力是不敢反對的,關鍵是做事時的心態別叫其鑽空子。」[4]
我審視自己的動機有沒有不純的地方,同時正告另外空間的邪惡生命:大法弟子在救度眾生,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允許干擾,誰干擾誰是罪,必須徹底清除。就這樣我發著正念順利的發完了資料。
因出門的機會少,我很珍惜每一次機會。我再次打破的是我平時送資料就不去發資料的習慣。那次我去給老阿姨送資料,除了給她的整包資料外,我還準備了自己回來路上要發的資料。到了阿姨小區門口,我給她打電話讓她出來接,我接連打了三次電話,都沒人接(沒提前給她約好,過去都是我直接送到她家裏。),我帶著這麼多資料還發不發?我猶豫了一下,立刻正念升起,發!這樣我順利的發完了資料。
三、破除對警察、居委會人員的觀念
還有一個突破的就是我對警察、居委會人員的觀念。在中共流氓集團二十多年的對大法與大法弟子的迫害中,這些人起到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急先鋒作用,天長日久,心中不由自主的把他們放在了救度眾生的對立面上,而沒有把他們當作是被迫害的眾生一員。
剛開始封閉管理的第一天,那時管的還不是太嚴,我和孩子結伴出去,回來時在門口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穿著警制棉服的年輕男子正對著一個居民大聲呵斥,態度蠻橫、惡劣。孩子說那人是個警察。因為門口保安穿的衣服也是類似顏色,我竟沒認出來。以後我每次出門都會遇到他,無論是中午,還是傍晚或其它時間段,我心裏不免有些膩歪。孩子說他們每個人負責一個小區,哪個小區有瘟疫了,哪個警察負責,他們都簽了責任狀的,所以他們才這麼認真執守。於是我就發正念清理,不讓我每次出門時遇見他。但不管用,我還是每次出門都能看到他守在大門口。我審視自己的心,發現我把關係搞錯了。我們之間不是迫害與被迫害的關係,是救度與被救度的關係。我雖然在目前情況下不方便給他們講真相,但還是要把慈悲留給對方。
那次出門檢查進出證的是物業的人,片警背對著我看著外面入門的人。我微笑著與物業的人打招呼:「你們可得保護好自己啊,天天接觸這麼多的人,太危險了。」聽到這話,片警驀的轉過頭來,定睛看著我,面無表情。我衝他微微一笑過去了。第二次出門,在門口我沒看見片警的身影。檢證的是居委會的人。我依然是微笑著打招呼:「你們辛苦了。」她深受感動:「你理解我們就好,理解萬歲。很快就會解封的。」我邊走邊笑道:「我們早盼著這一天呢。」剛出門,一看片警正專注的瞅著我呢,原來他在旁邊登記桌旁站著,聽見我的聲音才扭頭瞅我的。在法輪功裏我是他們的重點人物,我不知他是否認出來我,但每次遇到,他都非常注意我。
第三次出門檢證的正是片警,我依然微笑道:「辛苦了!你們該穿防護服的,這樣太危險了。」他無奈的苦笑了一下:「沒辦法,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做,我們也盼著早點結束。」
在近期學法中我也有所突破,在這裏簡單說一下,我修煉二十多年了,說來慚愧,《轉法輪》我斷斷續續的只背了三遍。現在讀法,根本就不入心,純粹走形式。我知道師父是讓我背法。我這次採取的方法是:按自然段背,太長的分開背。在手機上先抄寫一遍,有了印象了,然後再讀一遍或兩遍。覺的能背過了,再默寫一遍,有錯的更正過來,再背一遍,這樣個人感覺效果很好,能入心了。
以上是我近期的一段修煉體會,有不對的地方,請同修慈悲指正。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後的執著〉
[3]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二》〈怕啥〉
[4]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頓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