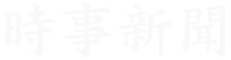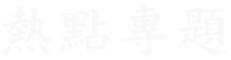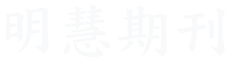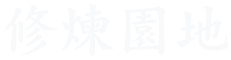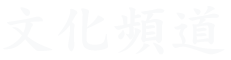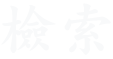黑龍江省七台河市郭其忠控告首惡江澤民
郭其忠是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在修煉前他患有胃炎、咽喉炎、鼻竇炎、風濕性關節炎、腰椎間盤突出等疾病,中西藥吃了不少也不見好轉。修煉後無病一身輕,為國家、家庭節省了一筆可觀的醫藥費。
郭其忠於二零零九年九月被綁架抄家,並被酷刑逼供,二零一零年四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七台河監獄慘遭毆打折磨。他的妻子被迫和他離婚,他的孩子也不敢和他聯繫。
以下是郭其忠自述的遭迫害事實: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八時左右,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新興區東風街,委主任萬金華,找我去街道辦事處簽字,說棚戶區所有戶主都得去簽字,當時妻子不在家去了南方,家裏只有我一人,只好答應了。我推著摩托車出了門看見萬金華正在打電話,看見我以後停了,她就坐著我的車往辦事處駛去,距辦事處二百米左右對面有一輛黑色轎車迎面開來。我剛進屋隨後進來兩個人把我架出去,塞進車裏向新興區東風派出所駛去。
到新興區東風派出所把我雙手銬在老虎凳上,所長趙孔偉,見到我說;這個老虎凳子多少年沒有人用過專為你準備的。他們沒有證據,沒有人來問過我。晚上六點多鐘拿著我的鑰匙,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他們六、七個人到我家抄家兩個多小時才回來,把我家翻的亂七八糟,到底拿走甚麼沒人知道,藏著最隱蔽的東西都找到了。拿到派出所看到的有:大法書籍,師父法像,電腦一台,打印機一台,手機一部,電子書一個,MP3兩個,身份證,銀行卡,準備給孩子的學費四千元,我哥的死亡證明(未消戶口),VCD一台,電視接收機兩個。還有可用的東西缺少甚麼也不清楚(我看到一個幹警拿著我用的微型礦燈往對面的抽屜裏放),他們像土匪一樣。
非法關押期間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准去廁所,不許睡覺。審訊時非法逼供,最後他們寫了無需有口供。二十三日下午三點多鐘,送往七台河看守所,連續兩次體檢不合格,體溫超標看守所拒收,隨後又去了防疫站,要求他們出個無險情證明,工作人員不給出,要求入診後三、四天後才能出結果。之後,強制讓我喝下冰水和不明藥物,秋天的夜晚刮著涼風,身上穿著單薄的衣服把我凍得全身發抖,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又去了看守所量體溫還是不合格。
所長趙孔偉請示上級,回覆是回來辦取保。他氣急敗壞的說;辦案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的事情,真是讓人笑掉大牙。到了新興分局又商量半個多小時,迅速返回市裏到二院,610、公安局頭目早就在那裏等候,連夜進行體檢,體檢完畢在旅店住一夜。九月二十四日早晨趙孔偉去醫院取出各科結果,又去了看守所量體溫還是高又拒收,為了迫害我他們可以升職、能得到高額的獎金,不顧人的死活,請示上級協商返回東風派出所又強制我喝下不明藥物,下午二點多鐘送往看守所,工作人員說,上面有令今天所有人都升高一度收所。其實當天只有我一人進入看守所,當時頭痛身體發燒嚴重。
在看守所裏幹警給有錢人買東西,有檢查的來通知把所有的東西藏起來。有一次,聽說檢查要來,犯人都忙著往板鋪下面藏,有一犯人拿一包小菜讓我給拿過去,管號的叫郎亞洲說太慢了,狠狠的打了我一個大耳光,當時眼睛發黑,耳朵嗡嗡作響,半個臉立刻腫了起來。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在七台河新興區法院非法開庭那天,我身體已經被迫害的非常虛弱,骨瘦如柴,有氣無力,滿口牙晃動、出血,因為不讓接見也沒有錢買牙具。修煉以前的疾病全都復發,如咽喉炎、鼻竇炎、腰椎間盤突出。咽喉炎、鼻竇炎惡化,化膿出血說不出話來,有時說出話聲音也很小;還有高血壓,心情激動時頭就發暈。自我辯護時我要求證人上庭對質、並且問他們:我做甚麼壞事哪個人看見了,那就讓他出庭作證。回答說沒有人看見。最後審判長說:「證據不足,休庭」。依照法律規定取證後再從新開庭,可是沒有。過了一段時間判決書下來了,我被冤判三年六個月。
在七台河看守所關押十個多月,送監獄前必須去警官醫院體檢。看守所陳所長親自督陣,在我的體溫高、血壓高時,連續拍了幾次片子均有異常影像時,是陳所長的「關照」,又一次強行把我送走。
二零一零年七月中旬到了七台河監獄集訓隊。由於血壓高頭經常犯暈,背監規我就記不住,集訓隊犯人班長郎亞洲用板條打,說是執行命令,打得全身是血印,連續多天。
還有兩個犯人班長,一個叫王成玉(七台河新建礦人),另一人姓施(雙鴨山人)。這兩人專為幹警拉關係,收、要犯人的財物給幹警,也為自己找出路。我從看守所到七台河監獄沒有接見任何人,也沒錢買東西,這兩個犯人找我要東西我沒有,他們記恨在心。有一次,幹活時在犯人的挑釁下對我進行一次毒打,他們兩個膀大腰圓比我高出一頭,那個手像鞋底一樣在後面左右開弓,往前走就給我拉回來,姓王的打完姓施的接著打,每人打了二十多下,打完後我兩眼黑黑的甚麼也看不著,身體晃晃悠悠,迷迷糊糊的坐在地上,不知是誰把我扶到座位上,當時值班幹警就在屋裏,任由他二人胡作非為,他們裝聾作啞,玩忽職守。
從那以後,我頭腦就不清醒、迷迷糊糊,睡覺腦袋沒有地方放,哪面朝下哪面就痛,血管要爆裂一樣,反應遲鈍。七台河監獄犯人吃飯時,都是站著隊到食堂去,去時報數回來時也報數,我幾乎每次都報錯,報錯了最少是一個耳光,為了報號天天被打罵。我四肢不靈,生活很難自理,就是被他們毒打造成的,這時轉監到了佳木斯監獄。
二零一零年十月中旬,我被轉押到黑龍江省佳木斯監獄八監區二中隊,監獄長葉楓下令中隊安排一名幹警和兩名犯人(其中一犯人叫王玉璽,是帶工的)對我進行轉化(強行放棄信仰),不同意就打(警察指使犯人打),打完再談(幹警談),白天和晚上都如此。有時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睡著了,王玉璽就用腳把我踹醒,有時還把腳跺在我的肚子上,我不敢睡就坐著,我的心臟病就是那個時候被他們嚇出來的。
還有兩位法輪功學員在此關押,其中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照顧我,為了進一步對我進行迫害,中隊長於春亮就把我們分開,讓七十多歲的老人出工,我留在監舍內。我的身體還是不好,行動非常困難不能自主,走出一步退回半步,左一腳右一腳,嘴歪眼斜,言語不清,四肢無力,頭疼痛難忍,迷迷糊糊總也不清醒,找幹警去醫院檢查治療推脫說沒錢。我吃飯連筷子都拿不住,放到嘴裏的飯只有三分之一;上衛生間連褲子都繫不上,有的看見就心煩,有好心的就幫一下忙,有的不幫忙甚至還踢一腳或打一拳或打一個耳光、嘴裏再罵一句那是常事。佳木斯監獄豢養牢頭獄霸,就在我身體這樣極度糟糕的情況下他們還逼我出工幹活,我幹不了又遭牢頭獄霸一頓毒打,我有多次被他們折磨的都有不想活下去的念頭。
因為我修煉法輪功,經過煉功後身體恢復的很快,是大法又一次救了我。他們就讓我在監內幫助打掃衛生,幫助抬飯桶。有一次抬飯正好趕上收工,被中隊長於春亮和帶工犯人王玉璽看見了就強制我出工,每天背著做鞋的材料上下樓來回幾十次,樓梯是鐵皮焊接的,人走在上面搖搖晃晃一不小心就容易掉下去。
二零一一年三月佳木斯監獄成立嚴管隊,是在集訓隊,要求轉化率達到百分之百,分兩期進行。我安排在第二批,提前做身體檢查,檢查結果有高血壓、心臟病、頭痛迷糊必須去市醫院檢查,說沒錢不去給做。第一批不到半個月被迫害死三名法輪功學員,他們就是秦月明、於雲剛、劉傳江。
我由於身體不適應出工就在監內管衛生(打掃水房)。二零一一年七月,監內水費交的不及時,犯人無水洗涮就偷水,被監獄發現,卻強制關了我七天小號,小號只有幾平方米,裏面陰冷潮濕,我在這裏受盡了折磨。後來有的犯人得了傳染性疾病住院,誰都怕傳染沒人願意去護理,他們就讓我去。
監獄為了強迫我放棄信仰,達到江澤民所要的轉化率,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中旬,七台河法院帶著我妻子來到佳木斯監獄與我離婚,我問她為甚麼要離婚?她說:「兩個孩子上大學、我還有糖尿病得買藥、交房屋貸款、我也沒有工作沒有經濟來源,去辦低保街道說法輪功家屬不給辦,我是實在沒有辦法才來離婚的,回去能辦個低保。」我知道離婚不是妻子的本意,是被江澤民的迫害法輪功政策逼的,如果我不同意離婚她就沒有辦法活下去,我懷著悲痛的心情違心的在離婚書上簽了字,把所有的財產都給她和孩子。是江澤民逼的我骨肉分離,是江澤民逼的我們結髮夫妻被迫離婚。離婚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本來身體已恢復的差不多了,從那以後頭部又開始劇烈疼痛、迷糊,這種狀態一直到出獄都沒恢復。
二零一二年中秋節後,中隊長於春亮傳信讓我出工,我到辦公室找他說明不能出工是我的身體原因,於春亮不容分說上來就打,並說讓你出工你就得出工,邊說邊不停的打我。我就喊:「警察打人了」。他就把我推到辦公室的單間裏接著打。這次毒打導致我心臟病發作,頭疼的更加嚴重,這次打我的整個過程大班幹警韓華、帶工犯人王玉璽全都看見了。
二零一三年三月,我冤獄期滿,釋放時已離婚的妻子找的車到監獄接我,當時的情景被監獄的監控錄了像,七台河市公安局找到前妻調查我的下落,我是正常釋放也不是逃出來的,七台河市公安局還多次找我、竊聽我的電話。本來我釋放回家後妻子讓我回家住,還給我買吃的補養身體。由於七台河公安去騷擾她,街道、派出所多次調查我、打聽我的下落。妻子迫於壓力不敢讓我回家,我現在沒有房子、沒有地、因為我煉法輪功的緣故,工作被開除沒有經濟來源,身體狀況又不好,只能幹輕微的工作維持生計,被迫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在我這裏充份展現出來。
在中共對法輪功近十六年的迫害中,我被非法關押三年六個月,我按「真、善、忍」做好人錯在哪裏?我只做好事,不做壞事,何罪之有?兩個孩子都考上大學,女兒考上公務員調查結果因為我煉法輪功,她不能被錄用,男朋友因為我煉法輪功與她分手。由於江澤民的株連政策至今兩個孩子也不敢與我聯繫,怕影響他們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