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勞教、判刑迫害 寧夏工程師謝毅強控告江澤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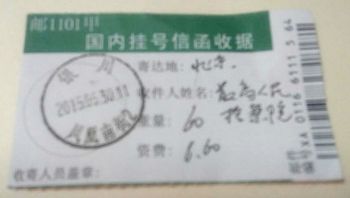 |
謝毅強,一九六四年七月出生,現居寧夏銀川市,曾被非法勞教三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謝毅強控告江澤民犯下酷刑罪、非法剝奪宗教信仰自由罪、誹謗罪、侮辱罪、綁架罪、故意傷害罪等罪行。
謝毅強所述事實與理由如下:
我曾被非法勞教三年,非法拘留七天,綁架到「610」強制洗腦二個月,非法判刑四年。
在這期間,曾被強迫超時奴工、用嘴撕咬有毒的膠(在銀川看守所),被整天銬在電線桿上任憑風吹、日曬、雨淋(在寧夏勞教所),勞教當時屬人民內部矛盾,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當時我已幾個月全身潰爛、流膿、流血,身體散發著極度的腐臭味,每天只能艱難的走幾步路,就是這樣也不允許這個人民內部矛盾的我保外就醫。
在銀川看守所我曾被四肢銬在鐵椅子裏,從腹到胸再用繩子緊緊勒在椅背上,全身只有頭能轉動,每天兩頓飯,一頓飯是半個饅頭和一蓋子水,吃飯時可將人放下上廁所,其餘時間只能拉、尿在褲子裏,低矮的小屋頭前是個大燈,日夜不停的照著。
在石嘴山監獄入監隊,在驕陽似火的七月間,我被每天早上六點多至晚上收工強迫站在監獄的操場上,等待著朝陽成為烈日,天天如此直至離開那個監獄。
在銀川監獄,我被侷限在指定的約1米×2米的框框內不得隨意離開,全監區的人不許和我說話,否則扣減刑分,晚上煉功時不時有人用拳打、用棍子搗。銀川監獄又請來了北京前進監獄的劉光輝一行,撕心裂肺的痛苦呻吟,也未能阻止他們對我的野蠻灌食,完好的凳子被鋸成十二公分左右的高度,我被強迫坐在上面,我只能腰挺直、胸拔直,兩腿收回並於身前,夜以繼日的坐著叫熬鷹,熬不住自有身前、身後的包夾人員「拳腳照顧」,還要日夜不停的看著大聲播放攻擊大法的各種片子,還達不到目的就有人用小棍子將我的兩個眼皮撐開,怕睡著了,即使這樣我還能睡著(更準確的應該是沒意識了),這時有人將我的眼皮翻開,用手指彈我的眼珠子。在恍惚間幹警拿來了一張紙讓我簽字,上面寫的是:我已經精神失常。幹警有時也會讓包夾我的人給我談話,可笑的是這些殺人、強姦、吸毒、搶劫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重刑犯人,給我大談人生意義,我卻只能聽著。
在這多年的魔難中,還有一個受害者─--我的母親,母親(姬芝蓮)也是一位法輪功修煉者,年輕時的母親曾在銀川市委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城區政府。母親日常生活中言語很少,但在哪兒都威信很高,曾被評為銀川市文明市民,工作中的各種表彰、榮譽證書更是一摞子,俗話講:「母子連心」,加之我們又是同修一部大法,每次我的被捕,母親總是徹夜難眠,無助、傷心、悲憤時常纏繞著這位善良的老人,她老人家每星期一甚至多次到看守所看我,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深切的思念,飛向高牆大院,飛進我的心田,那荒蕪的土地,那座陰森的冤獄,竟成了母親心靈得到些許慰藉的「寶地」,因為回去後她還要遭受世人的白眼,家人的埋怨與不理解,更有艱辛的不知方向的漫漫上訪之路。思念、艱辛、無望、悲憤終於拖垮了堅韌的母親,她老人家與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凌晨過世。
在所謂的「轉化」過程中,有北京前進監獄協助進行,有寧夏監獄管理局、寧夏610等部門參與驗收,這也從另一面證實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分工有序的、系統的迫害。
上學時我曾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工作後是單位最年輕的高級工程師,在謊言的宣傳下,卻是人人避之,我單位領導因我的問題,多次被要求寫檢查,只得到處表白以示和我劃清界限,這種株連也是對他人的人格尊嚴的侮辱,公安機關至今不允許我辦出國護照。在經濟上至今為止我已有十年以上沒有得到過正常的收入,身體上在勞教所、監獄兩次差點失去生命,嚴重時已經無法下地行走。這也印證了江澤民發布的對法輪功學員 「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
同時我也相信在這場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中,很多人是不知道真相的,或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想知道真相,然而自古道: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也希望諸位法官以正義之劍為自己開闢光明未來,做出正義的裁決。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5/6/18/1511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