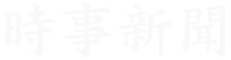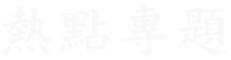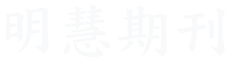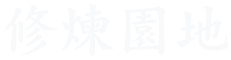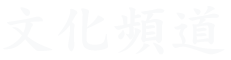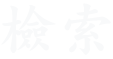山西忻州白瑞芳上訴開庭 法庭人員感動拭淚
山西省忻州城區白瑞芳女士二零零四年修煉法輪功後,起死回生,並獲得身心健康。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在回家路上被三名警察綁架,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被非法判刑三年。白瑞芳當庭提出上訴。忻州市中級法院本來於四月二十二日電話通知白瑞芳丈夫二十六日開庭,第二天又取消了開庭時間。直到五月九日,忻州中級法院又電話通知第二天(十日)開庭,白瑞芳的丈夫沒有答應,理由是法院違法,造成聘請的北京律師趕不來。當時邪黨法院的案件承辦人答應徵求北京律師的意見後再聯繫。在這種情況下確定了五月十日開庭。
二審法庭只有七個旁聽座位,多數親友沒能進入旁聽。
以下是白瑞芳的上訴書及其丈夫的辯護詞摘錄:
上訴書(摘錄)
上訴人白瑞芳,女,1960年5月20日生,漢族,五寨縣梁家坪鄉水口頭村人,住忻府區檢察院宿舍。
我是法輪大法(也叫法輪功,簡稱大法)修煉者,大法教我按照「真、善、忍」做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按照自己對「真、善、忍」的理解行事。
我是2004年修煉法輪功的。此前我有貧血(最嚴重時全身只有5克血色素)、過敏性鼻炎、多種婦科病、哮喘。整天除了跑醫院、收集醫藥信息外,就是求神拜佛或練氣功(後來知道是假氣功)。花了不少錢,結果病情越來越重。到了2004年8月,哮喘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每到晚上呼吸困難,不但自己不能睡覺,攪擾的家裏人都不能安生。於是到山西大學二院住院治療,期間每天花銷1000多元醫療費,一週後,帶的錢花光了,而病情並無好轉。由於難以承受對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的醫療費,我便要求出院回家。後來丈夫說,他那時已經做好我的後事打算了:回家後買個小型人力三輪車,天氣好的時候,他拉上我到街上轉悠轉悠,等我死後(他估計我活不了幾天),就帶著孩子回原平老家。是天不絕我,從醫院回家後不久,我有幸得到大法書籍和音象資料,開始煉法輪功。
不到三個月我全身的病不醫而癒,那真是無病一身輕。從此丈夫從我的全職保姆中解脫出來,恢復了久違的家庭和諧氣氛,孩子像從精神枷鎖中解放了一樣,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從此我堅信法輪功是正的好的功法,隨著學法我知道了這是救世救人的佛法。我一邊自學法輪功理論,一邊按照對法理的理解指導我做個好人。我從法理中知道,現在人類受無神論的影響,不相信善惡有報,為所欲為,幾乎沒有道德底線,所以不久會有人類大淘汰,越來越多的天災人禍只不過是對人的警示。法輪功的傳出,在常人社會中是大法弟子修煉(從做好人做起,不斷提高道德水準,提高層次)和大法弟子在大淘汰前救人。實踐中大法弟子講真相、發資料就是救人。所以我也要做這些救人的事情。
從法理中我知道,大法弟子能夠按照法的要求做時,師父就會保護的。我為甚麼沒有得到師父的保護呢?肯定是自己沒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首先考慮別人,並且要求大法弟子用純淨心態、無為狀態、完全為了救人去做,同時還要求大法弟子的言行符合常人狀態、又不能觸動常人的負面因素。從法中我還知道,一個人能否被救,主要取決於此人對大法或大法弟子的態度。痛定思痛,深刻找自己,我是抱著做事的心、強加於別人的心、對不同的人有分別心去做,根本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完全是常人狀態。師父保護的是修煉人,怎麼會保護我這個常人呢?更為痛心的是,由於自己沒有做好,導致警察對我抓捕、檢察官對我批捕起訴、法官對我判刑,造成這些人對大法的負面態度,不但沒有救了這些人,反而可能造成他們失去被救的機會而被淘汰。這不是和大法的要求相反嗎?因為師父講過,世上的人都是師父的親人,絕大多數是應該救度的。現在想來我真的對不起他們。如果能用我的承受來換取他們對法輪功的正面態度,我是甘心承受的。
以上是我近一段時間對自己的反思和認識。
至於五寨縣法院對我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我認為缺乏法律依據。關於在法律層面上的上訴理由,在原審五寨法院庭審中我丈夫為我辯護時的辯護意見已經說清楚了。
原審判決書以刑法三百條對我判刑,也沒有指出我的行為破壞了國家哪一條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實施,這就像指控一個人犯了殺人罪而不存在被殺的人一樣,具有「莫須有」之嫌。
此致
忻州市法院
上訴人 白瑞芳
2013.1.31
辯護詞(摘錄)
我作為白瑞芳的丈夫,受其本人的委託依法為其辯護,從我的親身感受,我認為白瑞芳受到刑罰處罰既沒有法律依據又天理不容。沒有法律依據的問題,第一辯護人已經論述清楚,我同意第一辯護人的意見。我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講為甚麼天理不容。
1、白瑞芳身體的變化改變了家庭環境,使全家人從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
煉法輪功之前,白瑞芳患有多種婦科病、過敏性鼻炎、貧血、哮喘等病。貧血嚴重時全身只有5克血色素。尤其是哮喘病,呼吸困難,晚上不能睡覺。到處求醫問藥,不見明顯效果;多處求神拜佛,也不解決問題。由於病魔纏身,加上經濟負擔,導致她本人情緒悲觀,性格暴躁,兩個孩子成了她的出氣筒,我成了她的全職保姆,全家人整天生活在壓抑、擔心、無助、絕望的氛圍中。在精神和經濟兩方面的壓力下,我度日如年。
煉功不到三個月,她全身病不醫而癒,八年來沒有吃過一粒藥,不但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而且還創造了可觀的經濟財富,更重要的是使全家人回歸到正常生活中來。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每一個正常人面對這樣的事情會有甚麼感受!心情的改觀,精神的解放,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會把精神財富轉化成多少物質財富。如果有很多這樣的家庭,那還不是真正的安居樂業,其樂融融的社會景觀嗎?
2、白瑞芳精神的變化,使惡化的婆媳關係逐漸融洽。
煉法輪功前,白瑞芳與我母親是水火關係,當然是兩方面的原因。我不想斷言誰是誰非,只講述一件事情:在白瑞芳生我女兒的月子裏,因我母親的言行使出生十幾天的女兒沒了奶水,好不容易捱到40天,我看實在不能呆在家裏了,在過年前的臘月十九我自己拉上小平車把母女倆拉到相距十五里我任教的崞陽中學去過年。臨走前我把40天所用1.6元的電費還得給母親留下。難怪白瑞芳曾多次嚴肅的對我講過「我死後不進你家墳」。但是她修煉後對我母親的態度發生很大改變。有些事現在想起來我還不能平靜,可她認為要按真善忍做人,對別人首先要忍讓,同時要用別人的優點來對照自己的缺點,使自己做一個越來越好的人。修煉後她每年都要給我母親買一兩身衣服並回家看望老人,回家後總是盡力幫老人做一些事情。2008年的一次回家,母親拿出一千元錢給她,並說「三個媳婦最虧待你了」,三番五次硬把錢塞到她包裏。
我們知道,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這樣的家庭就是社會中的抗癌細胞,如果出現大量這種家庭,那才是真正的禮儀之邦,是中華盛世。
3、白瑞芳境界的昇華,約束我道德不那麼下滑。
在當今一切向錢看的潮流中,我受利益的驅動,一些「額外進項」對我本人和家庭還是接受的。但是在白瑞芳修煉後,逐漸使我淡化這方面的慾望,成了不符合潮流的人。舉一個例子:2009年我辦理忻府區紫岩鄉紫郡村委申訴的民事案件,到2010年農曆新年時,紫郡村委幹部通過別人送到我家裏一箱酒,兩條煙和一些水果。送禮的人走後,白瑞芳提出,年後要給村幹部送回去。我想這不是甚麼大事,就說「那有點不近情理了吧」。她說「村幹部想辦事才送東西,他花的是集體的錢,如果事情辦不成,你叫他怎麼向村民交代。東西不在多少,道理一樣。法中要求遇事先考慮別人,否則就不是用法對照了」。我不喝酒不抽煙,不是看重這些東西,主要是不想陪她到村裏一趟。所以動員她「水果放到年後會壞掉,現在自己吃了,到時折錢還吧」。一過大年,她就催我初八上班前去紫郡村送這些東西,我找藉口沒有去。之後又催我幾次,我都找理由推辭了。過了正月十五又催我,並說「你不願意去,我自己騎摩托車去」。我只好陪她把東西送回去。後來村幹部又要送我一張3000元的卡。我沒有要。
白瑞芳煉功後,她盡力按照自己對真善忍的理解要求自己,不只是一種外在表現,確確實實是她內心的反應。她不只是要求我不收當事人的東西,也不讓我吃當事人的飯,而且一再要求我好好工作。前一段時間公訴人上看守所向她做材料時,她還請公訴人轉告我要好好上班,不要以為她影響了我的工作積極性。我會見她時,她對任何人沒有怨言,而是從內心找自己的問題。她認為走到現在的主要原因,是她自己以前沒有嚴格的用法來要求自己,很多做法沒有站在法上,結果傷害了別人,還使自己走了彎路。本來她的所言所行完全是想為別人好,她希望接觸到她言行的人,雖然不可能像她那樣嚴格用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可是只要能做一個好人,就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諧的家庭,還會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對個人、國家和社會都是有益的。
我想,如果我們公職人員的家屬都像白瑞芳那樣,我們國家還會有那麼多裸官嗎?還會有買官賣官、權錢交易、貪污受賄嗎?(注 這時審判長阻止了以下內容:還會有社會不公嗎?還會有毒大米、毒麵粉、毒蔬菜、毒奶粉、地溝油嗎?還會有仇官仇富現象嗎?還會有警察告訴自己的孩子不敢說有個警察爸爸嗎?等等。)這樣的人被審判符合天理嗎?可是今天這樣的人就站在被告席上被審判,而且失去自由半年多了。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做這樣的事情自己的道德良知還有多少?中國人講善惡有報,這樣的做法會有善報嗎?中國人還講積陰德,我們是給子孫後代積德呢,還是造罪呢?
多數公檢法的辦案人認為,法輪功案件是政治事件,得服從上邊的命令。政治事件更應該依法辦事呀。回顧我們國家的歷史,每一次政治運動都不脫離「迫害─平反─清算」的規律。我在一審時向法庭陳述過現行的所有法律都沒有規定法輪功是邪教,並提供了2005年公安部和國務院重新認定的14種邪教中沒有法輪功的證據。我們想一想從1999年迫害,時隔6年,我們國家為甚麼會重審沒有法輪功的14種邪教呢?很明顯當時的胡溫政府要與迫害法輪功切割,據說溫家寶曾三次提出平反法輪功。
如果法輪功問題也遵循迫害--平反─清算的規律,恐怕清算的時日不可能太久了。我們真的應該理智的想一想這個問題了。真心希望參與本案的人們,都能喚醒良知,懲惡揚善,這樣一定會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