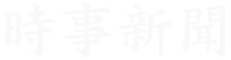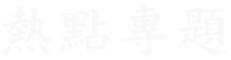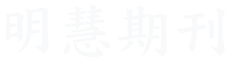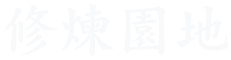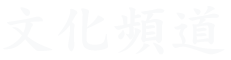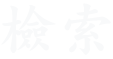曝光多年來惡黨對我的迫害
得法前我滿身是病,腦血栓前兆、尿路感染、腿疼、胃病等等。通過學法煉功,這些病痛都不翼而飛,用同修的話講,「你真是換了個人」。並且一改過去的暴躁脾氣,慢慢變的祥和了,我真正的感受到大法的超常與師尊的慈悲苦度。
一九九九年七月,對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鋪天蓋地的邪惡迫害開始了。為了證實大法,我們幾個同修堅持在公園裏煉功。幾天後被劫持到白山路派出所,逼供一天一宿,後被劫持到遼寧省大連市戒毒所非法關押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末為給大法說句公道話去北京上訪,在旅館被綁架,第二天被劫持到大連市戒毒所。在戒毒所,大法弟子每天被強迫背手坐,強迫聽誹謗師尊、誹謗大法的錄音,強制洗腦。
為抗議對我們的無理迫害,我和幾個同修開始絕食。惡警老莊用木板狠毒的打我,身上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八天後我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幹奴役,二十四天後被劫持到大連教養院非法勞教兩年。
在大連教養院,為了抵制迫害,我們八十個同修集體絕食,遭到惡警殘酷迫害。每天被灌食兩次,被惡警毒打,惡警林儀用電棍電。二十七天後,大法弟子孫連霞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以司法局副局長郝寶昆為首的邪惡之徒對大法弟子的強制「轉化」開始了。晚上所有大法弟子都被強迫彎腰九十度、兩手後伸站著,強迫踩寫在紙上的師尊的名字。同修被輪番帶到走廊裏,簽「轉化書」。走廊裏皮鞭聲、刺耳的電棍聲、大法弟子的尖叫聲及辱罵師尊和大法的廣播聲混在一起,一片恐怖。迫害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上午。由於當時法理不清,面對邪惡的暴力「轉化」兩名同修為反迫害被迫跳樓,做了違背大法法理的事。
同年六月,又一輪強制「轉化」開始了。一天下午,我清清楚楚的聽到惡警韓健敏告訴猶大「動手」。晚上我被帶到儲藏室,一幫猶大用塑料拖鞋底、拖布把等毒打我,當時能用來打人的東西全用上了。體罰、不准睡覺,連續兩天我被打的頭、臉、身體全部腫脹、青紫。這次強制「轉化」,大法弟子王秋霞被猶大用裝滿水的可樂瓶子活活打死。當時,惡警苑玲月值班,王秋霞喊「救命」她也不管,王秋霞被打死與她有直接關係。
二零零二年過年期間,因我悟到不應該呆在邪惡的黑窩裏便絕食反迫害,被惡警毒打、關小號迫害。在小號裏,被強迫罰站、戴手銬、不准睡覺、開窗凍、睡死人床等,腳腿被迫害的腫脹、麻木,四防還穿鞋踩我的臉,在這種野蠻折磨下,我被迫害得肝炎,保外就醫。
回家後不到五十天,四月十八日教養院四個惡警到我家將我劫持到教養院,我再次絕食。惡警韓健敏惡狠狠的說:「大連教養院沒有人敢絕食,你絕食給你灌酒養胃。」他們把我拖去連續兩天用鼻管給我灌啤酒兩次。見我仍不吃飯,韓健敏高聲喊著「明天給她灌燒酒」。第三天真的給我灌了燒酒。因我不配合邪惡,他們用力撬我的牙齒,致使我前面的牙齒全部鬆動,並露出很大的縫。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在惡警萬雅林的指使下,四防把我吊起來,以五馬分屍刑罰進行性迫害,那種折磨真是撕心裂肺。他們還用凳子尖抵住陰部轉,幾個惡人輪番轉,邊折磨邊問「吃不吃飯?不吃再灌酒!」。看我昏過去了,他們就往我臉上潑水,拳打腳踢,直至筋疲力盡。幾個小時過去後,把我放下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他們卻問我恨不恨他們。第二天我的下身全部青紫腫脹並流血不止。我要求上醫院,他們把我帶到中心醫院,醫生問我是怎麼回事,惡警謊稱是磕的,醫生說:「不可能,這是一個特殊的病人」並讓惡警走。我對醫生講述了被迫害的經過,並要求住院。第二天惡警將我送到醫院交給我女兒後就逃之夭夭了。我女兒見我被迫害成這樣,氣憤的給教養院打電話:「你們把我母親迫害成這樣,我要一直把你們告到聯合國去!」
在我被迫害期間,女兒曾多次到派出所、看守所要人,被白山路派出所非法關押幾個小時,片警張學東多次上門騷擾,勒索女兒五千元錢,並恐嚇,威脅要沒收她的身份證。在這種強大的精神壓力下,女兒承受不住,導致精神失常。
二零零五年我外出發放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密,被綁架到派出所,後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絕食被毒打,惡警往我嘴裏塞報紙,被迫害的昏迷不醒後送中心醫院住院,三天就花了一萬多元。
還有一次,我回老家,因講真相被告密。石河派出所賴姓警察將我綁架到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被劫持到金縣三里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十天。在看守所因煉功被惡警毒打。
我在家期間,片警、居委會、街道多次上門騷擾、恐嚇,以致老伴憂心忡忡,精神恍惚。
二零零七年大連達沃斯會議期間,白山路派出所多名惡警、片警王興民、陳姓女警,集賢社區周姓男工作人員、丁姓、劉姓女工作人員、王梅芳、郝運來(音)以及其它不知姓名的人前來我家騷擾,在走廊裏監視三天。
奧運前,集賢社區周姓男工作人員、郝運來(音)等在走廊監視,並非法抄家,抄走大法書籍和私人財產。社區丁姓女工作人員還威脅我兒子,「以後有甚麼事情你母親都在數。」
二零零九年「四﹒二五」這天,集賢社區丁姓女工作人員、郝運來(音)及派出所陳姓警察等又來監視一天。我問它們來幹甚麼,一人說是保護居民安全,另一人說,「跟你說實話,就是來看著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