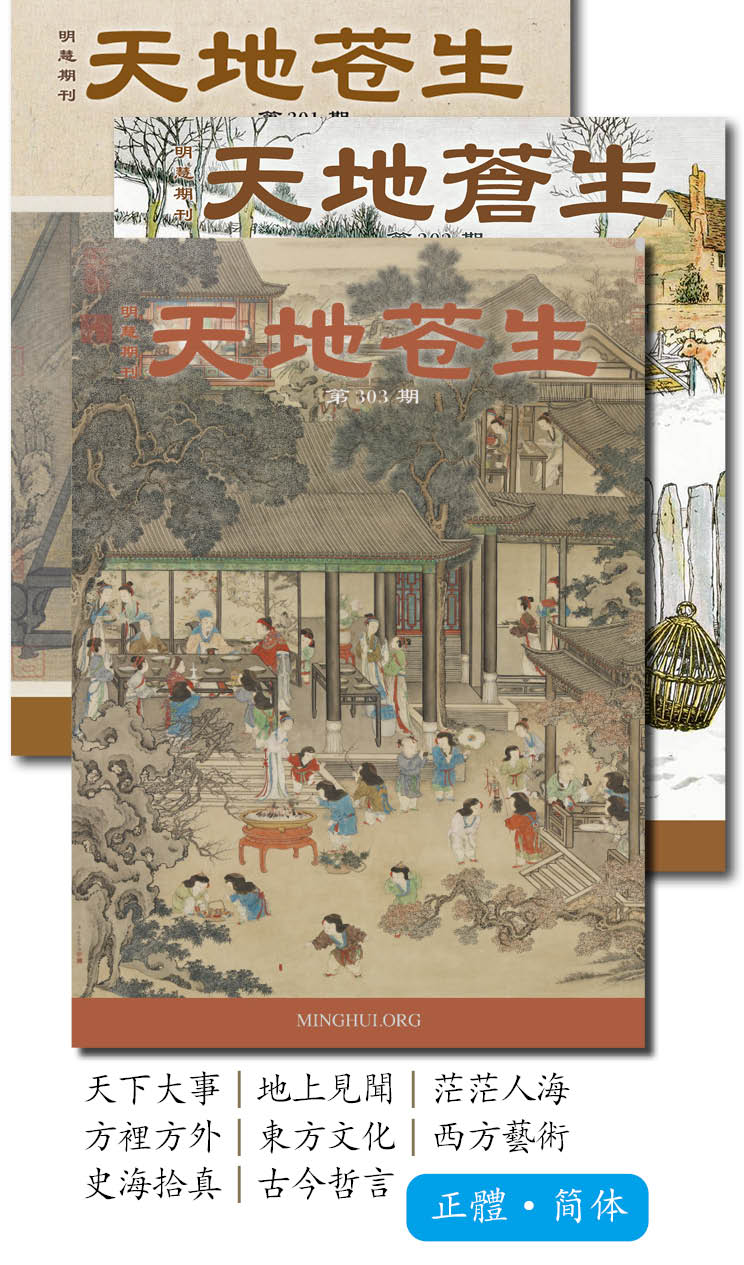門秀美一家人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風雲突變,黑幫亂黨開始打壓法輪功,誹謗師父。我心裏難受極了,這麼好的功法,政府不讓煉,不分青紅皂白的打壓、欺騙、造謠、誣陷、栽贓陷害等等,我們心裏都很不平,都上北京去找政府,告訴他們法輪功是好的。
我們一家去了五口人,誰知到了北京,還沒找到政府就被惡警抓起來了,把我們送到了駐京辦地下室非法關押七天,又送回原地拘留十五天,說是十五天,進去就是無限期的非法關押,已經非法關押了三十天還不放人,最後經過絕食抗議,才把我們放出來。在這期間,我們全家也都悟到,應該走出來向人們講清真相,叫人們知道法輪大法是好的,是最正的,就這樣我們多次去北京講真相、打橫幅。
在初期的時候,我們對法學的不透,悟性差,也多次被邪惡抓起來拘留。我記得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和兒子、孫子、兒媳婦一起去北京打橫幅,我被抓後關押在北京石景山拘留所,因為當時不報姓名,半夜提審時,惡警為我不報地點、姓名,一個又高又胖的惡警用力的猛打我的臉,左右兩面一齊打,這時我的臉就腫起來了,嘴開始往出冒血沫子。
我的歲數比惡警的母親歲數大的多,惡警打我打累了,又有另一個偽善的惡警把我領到另一個房間,對我說:「老太太,我們知道你們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家裏也很困難,你說實話你是甚麼地方的,明天一早我就把你放了。」我被邪惡欺騙,告訴了他我是雞西的。第二天,他們把我拉到了駐京辦的地下室,專門抓捕關押各省、市大法弟子的地方。
在駐京辦地下室中被非法關押了三天,我被帶著刑具手銬,押回了黑龍江省雞西拘留所,遭到了酷刑折磨。惡人們讓我寫「轉化書」,我認為修煉真善忍沒有錯,我們認定大法是好的,是最正的。我不寫「轉化書」,結果又非法拘留了我二十天後,非法判了我一年勞教。
我被非法勞教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七點,惡警把我從雞西拘留所提出來,拿出他們早就寫好的筆錄讓我簽字,我說簽字幹甚麼?他們說判你一年勞教。我說我沒有罪,我不簽字,片警小佟說:「這事由不得你了,你簽不簽字都得判你勞教。」就在這三九天刮著西北風的夜晚,惡人們給我戴上手銬,往哈爾濱萬家勞教所裏送。我已經絕食四天抗議轉化,基本上有氣無力的我,再加上衣服單薄,我在車上幾次凍僵了,背過氣去。
到了萬家勞教所,我在勞教所受盡了惡警的折磨,吃飯不報數不讓吃飯,三伏天在太陽地曝曬,面牆罰站,不讓上廁所,不讓吃飯等等。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一起背《論語》,被惡警暴打一頓,我摔倒在地上還沒爬起來,又被惡警穿棉皮鞋踢斷了我一根右肋骨,三個月才好。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七日,惡警編了六條所謂的監規:不上訪、不煉功、不上北京等等,叫大法弟子簽字,大法弟子拒絕簽字。當天夜裏,惡警就毒打老三班的十五個大法弟子。二樓有一個李姓大法弟子,是開著修的,他就說了一句:「一樓打死人了。」被刑事犯獄頭聽到後報告給了惡警。六月十八日早飯時,惡人們買來了四個菜一碗米飯讓李同修吃,李同修想為甚麼叫我吃這樣好的飯菜?惡警們四五個人催著他吃,這是李同修耳邊有一聲音告訴他:「有毒。」李同修對惡警們說:「你們先吃我就吃,你們不吃我也不吃。」就在這種情況下,惡警們把這位李同修送到密室去了。當時據說這十五個人有打死的,有沒打死的,全都被拉到了密室藏了起來。後來才知道當時死了四個人,其餘十一個人都活了過來,這就是萬家勞教所的「6.18事故」,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都知道的事,現在慘絕人寰的迫害還在持續。
這時我在裏面已經被折磨的生了一身疥瘡,癢癢不堪,又加上吐血、拉血,不能進食,我奄奄一息,覺的自己不行了。有一天我想打打坐調理調理身體,結果被監號小馬看見了,報告到了勞教所林隊長和大隊長武金英那裏,很多惡警都來了,加上小馬五個人一起整我。我說我就煉煉功調理一下身體,惡人們說啥也不行,說這是政府不讓煉的,我說政府是誰,不就是江邪惡不讓煉嗎?林惡警說:「江××的名是你叫的嗎?」我說江××的名不讓叫它起個名壓著好養呀!再說我就到天安門說了一句真話「法輪大法好」,你們就這樣折磨我。惡人們自知理虧,無話可說,林邪惡就用拳頭狠搗我的前胸,一直好幾個月我都不敢喘大氣。
還有一次,那是二零零一年正月,我在煉功時,被號長相緣琴看見了,把我叫到三樓,連罵帶折磨我。第二天她下樓在樓梯上滑倒把胳膊摔斷了,住院好幾個月,我想這都是她的報應。
到了陰曆十月一日,每個大法弟子胸前帶一枝小白花,紀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
由於我身體越來越不好,邪惡怕我死在勞教所,在十一月十七日把我釋放了。
老伴程謀忠的遭遇,我被第二次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老伴多次去北京證實法被非法關押、拘留,遭受了很多酷刑的折磨。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我和老伴晚上在家裏看講法,兩個惡警闖進屋去,搶我們的寶書,我們就是不給,在這時突然「喀」一聲停電了,片警小佟和劉明貴罵罵咧咧的走了。
第二天這兩個惡人又來我家,又給老伴寫筆錄,向老伴要這本書。過了幾天,大約是十一月末,一下子七個惡警闖進我家,瘋狂搶奪我們的大法書,又叫我們穿好衣服拿著行李,說是讓我們去見所長。我說見所長拿行李幹啥?現在明白惡警們要幹甚麼了,老伴寧死也不跟他們去,這時上來兩個惡警把老伴架著拖上車,老伴沒穿鞋,掙扎不過他們兩人。這時惡警又強行拉我上車,我掙扎著不去。
他們硬把我們拉到了車上,送到了恒山分局,作完筆錄後,我再次被非法判刑一年,老伴被非法拘留。第二天惡警到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十七本大法書,一萬二千元現金都被搶走,連收據手續都沒有。
老伴過著流浪的日子,直到我被釋放,老伴把我從萬家勞教所接出來,惡人還是天天騷擾我們,沒有辦法,我們老倆口只好離家出走,在外面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
兒子、兒媳和小孫子的遭遇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兒子程佩明和兒媳王淑紅、孫子程玉,還有另一位姓王的夫婦及孩子一起去北京證實大法,打橫幅,結果大人都被惡警抓走,只剩下我那九歲的小孫子程玉和另一個姓王的小孩。兩個孩子沒有了主心骨,兩人商量著想到車站買票回家,從北京到雞西車站,好幾千里地,還要倒車,十幾歲的小孩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門,這可是個大難題。小程玉說:「小哥,咱倆幹甚麼來了?」另一小孩說:「咱倆不是來打橫幅的嗎?」程玉說:「我的橫幅還沒打開呢」小孩說:「我的也沒打開。」程玉說:「咱倆再回去打開嗎!」「好啊!」
結果這兩個孩子又回到了天安門廣場,程玉說:「這回咱倆分開打橫幅,小哥你去金水橋,我上天安門廣場好不好?」「好。」姓王的小同修同意了。小程玉到了天安門廣場,把自己身上的橫幅打開,高喊「法輪大法好!」喊了三聲就被惡警抓起來了,惡警問他:「你這麼點小孩誰領你來的?」程玉說:「我爸和媽領我來的。」「你爸爸和媽媽上哪去了?」程玉說:「都叫你們抓走了。」「抓哪去了?」惡警問。程玉說:「不知道。」「你是甚麼地方人?」程玉說:「雞西的。」
警察領著程玉找遍了北京城所有關押大法弟子的鐵籠子,也沒有找到他的父母,最後把孩子押到了天津拘留所,在天津拘留所裏,遇到了一雞西大法弟子,也是從北京被抓到這裏來的,趙姨認識小程玉,便將程玉領回了雞西。
兒子程佩明的遭遇
兒子程佩明工作下崗以後,就和媳婦一起去了山東即墨市的一個農村做小本生意,三口人過的紅紅火火的。程佩明自從煉法輪功後,身上一切的病痛都不翼而飛,以前的肺病完全好了,身體健康了,生活方面都很順心。
可是好景不長,就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打壓法輪功之後,他們全家的好日子完全被江邪惡集團給拆散了。那裏的邪惡之徒不讓他們做生意,攆他們離開那裏,強制他從自己的家蹲著走,惡人擰著他的耳朵一步一步的走到鄉政府,大熱天累的他休克了好幾次,不讓他喝水,渴的嘴唇都裂了口子,惡人還對他連踢帶打,就是不讓他煉法輪功。
程佩明當時想:我的生命是師父和大法給的,我這麼重的肺結核不吃藥都好了,我怎麼能不煉功呢?而且那電視上徹頭徹尾都是在造謠誹謗大法和師父,都不是真的,我們都是真正的受益者。當時他的心很堅定,不配合邪惡,就這樣被當地的惡人強行趕回了東北。
在大慶住了半年,結果「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又被大慶的惡人攆回了雞西老家,在張新礦同我們老倆口住在一起。真是走到哪裏中共邪黨都不讓做好人。
一天晚上,邪惡又要抓兒子,結果沒抓著,從此以後兒子就流離失所了。為了證實大法好,他和幾個同修一起做起講真相的事,做真相資料,救度被邪惡欺騙的眾生。有一次,他和幾個大法弟子一起作真相資料被壞人舉報,幾個人全被邪惡綁架,搶走了好多大法書籍,還有一輛出租車,真相資料等,程佩明被非法判了八年的重刑。
程佩明在受到的酷刑折磨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程佩明被非法判重刑八年,在這期間,他受盡了惡警的殘酷折磨,以下是他舉證五個地方的迫害事實。
舉證(一):
地點:黑龍江省雞西市雞冠區公安分局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一日,我參加雞西市雞冠區紅星鄉大法弟子的法會時,被兩名惡警綁架,接著又上來兩名惡警,沒問我任何問題,就對我一頓毒打,打得十分嚴重,將我打倒在地又拖著我的腳向警車那邊拖去,共拖了八十多米,他們把我抬起來硬塞到了桑塔納警車的後備箱裏。我用力掙扎,頭部正好墊在後備箱的鐵楞上,惡警們就對我的頭部一頓猛打,把我打進後備箱裏後,車開到了雞冠區公安分局,把我扔進了一間刑訊室內,當時是下午四點。
從五月十一日四點開始,四名惡警採用各種殘酷的刑訊手段折磨我,一直持續到五月十三日上午八時,長達三十多個小時,期間除了他們吃飯的時間外,一直沒有間斷過。在整個行惡過程中,他們始終沒穿警服,害怕我揭露他們的罪行。現在我把這四名惡警對我殘酷迫害的過程揭露出來。
惡警們把我綁在老虎凳上,用十多種酷刑來折磨我,有用拳打我的臉、「拿麻」、「太空帽」、火燒竹籤扎指甲、皮筋抽嘴、皮帶夾刮剔肋骨、銑頭搓乳頭、警棍砸、摳鎖骨等。
「拿麻」,是四個惡警同時對我迫害,其中兩個惡警用雙手摳大腿根,另兩個惡警用攥拳突出中指從兩肋底部一直搓到腋下,極其痛苦,渾身虛脫。
「太空帽」,是先在頭部套上塑料袋,戴上鋼盔,用七斤重的鐵錘猛砸鋼盔,使大腦受到強烈震盪,處於昏迷狀態,然後將鼻部塑料袋摳破,進行逼供。
惡警們給我戴的手銬和腳鐐重達四十斤,晚上睡覺時也不卸下。我對裏面的其他犯人說:「法輪功無罪。」說完就開始絕食抗議迫害。犯人天天打我。五月十五日,副所長張義來勸我進食,我不同意,他就讓我給他跪下,我說大法弟子不給常人下跪,兩名犯人就強行按我的頭向地上撞去。惡警張義領著四名惡警用電棍打我,並把我的衣服扒光,電我的小便處,電我的嘴部,強迫我罵老師、罵大法,我不罵,他們就連續電了我三天。我實在承受不住,開始進食了,他們把腳鐐換成重達六十斤的給我戴上,共戴了二十四天。在一個月內,張義還時常指使犯人對我進行迫害,有往我臉上吐痰、批鬥、往嘴裏塞不洗的臭襪子、毒打等。大年初七那天沒有任何原因,我又遭到了張義的電棍毒打。
舉證(二):
地點:雞西市第一看守所
五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我被投入雞西第一看守所八號監。管教對監號內犯人交代說:「這是雞西法輪功二號人物,好好幫幫教。」犯人都知道他的意思,我剛進號內,兩名犯人對著我的頭部一陣重拳,我一頭撞向牆壁,他們就將我抱住。管教從監控中看到這一切,開門進來,給我戴上了手銬和腳鐐,重達四十多斤。
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長達十一個月,全身浮腫,所裏的王大夫說:「法輪功被迫害死了,就是開個死亡證明,說有病致死。」
舉證(三):
地點:雞西市雞冠區法院
二零零二年元月,在雞冠區法院開庭,我在法院對審判員說:「法輪大法沒有錯,是正法,我們沒有罪。」他們強行非法判了我八年,法警打了我五警棍。
舉證(四):
地點:哈爾濱監獄,以下簡稱「哈監」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我被投入了哈監集訓隊,惡人們從精神和肉體上對我繼續迫害。
二零零三年元月五日,林波逼我寫揭批材料,不寫就關小號。我為了不揭批,反迫害,吞入了七釐米鋼針六枚(編者註﹕大法弟子反迫害要正念正行,不必用這種過激的方式。)兩次去省醫院取鋼針。我在醫院講真相,手術前對主治醫師及小護士說:「我師父是道德表率,法輪功不是×教,我們都是好人,我求你告訴他們別迫害我們了。」在場的哈監幹警林皮、杜作聖、李才等五人都低下了頭。
在手術中,從我胃中抽出了二盒淤血,鋼針已經扎在了腸子上,手術兩個多小時,腹部手術時沒麻藥,胃腸造成嚴重損傷、出血,手術時一直頭暈、迷糊,四肢無力。
從醫院回到了哈監醫院,僅打了兩天點滴,在第三天中午,林波、董志民、張久珊幾人就把我關進了小號,我進小號後開始絕食。晚上犯人張勇、張曉峰、倪傑進入小號迫害我,張勇說:「程佩明你別怪我,這是政府讓的,打死了政府頂著,打不死只要整好,我們就立功。」然後用長毛巾勒住我的嘴,用手指彈我的眼珠、用雙拳猛擊我的兩耳、用手捏我的睪丸、摸後背脊梁骨骨縫、用腳踢我頭部。張勇摳我的鎖骨,使我的半個臂膀發麻,極其痛苦;倪傑、張曉峰踢我的兩側軟肋、掰我的手指,一直這樣殘酷的折磨了我數個小時,我嗓子發乾,往外嘔吐東西,因為嘴被毛巾勒住沒有吐出來,又倒流進腸胃裏。後來他們怕出人命,找來了惡警,又把我送回了醫院。事後我找林波、黃志峰反映我在小號被打一事,他們不聞不問,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舉證(五):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我被下到六監區,我正式提出要控告集訓隊迫害我的惡警,我向大隊長朱文臣反映我被迫害的事實,他害怕說:「你們破壞鑫諾衛星是違法的。」我說:「如果你讓我們在監獄大法弟子到中央電視台說明事實真相,世人十人有九個會學法輪功的,現在我們說真話的被關押在監獄受迫害。」惡警們說:「你別告了,法律是講證據的。」我說:「我是第一受害人,我的證據有,我吐在被子上的血跡還有。」他們說:「你有肺結核,那是肺結核吐血。」這真是有冤無處伸,打官司有天大的理也打不贏,還得把你抓到監獄裏去,這就是中國大陸共產邪靈領導下的邪惡勢力,專門打壓手無寸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做超常好人的大法弟子。
以上是我兒子程佩明受到的迫害事實,二零零四年年底,兒媳王淑紅一人帶著十多歲的小程玉無法生活,她提出了離婚,到監獄去辦理了同程佩明的離婚手續。現在我的大女兒和二女兒還在哈爾濱女子監獄受著迫害,每天幹著超體力的重活。
我們這一家人被江××邪惡集團害的父南子北,妻離子散。我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從我一家人遭受的迫害中,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不要再被中共的謊言欺騙。在天滅中共之際,脫離中共,為自己選擇好的未來。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7/5/13/85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