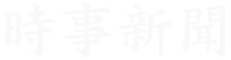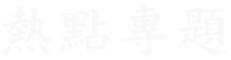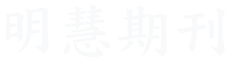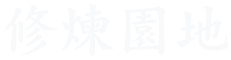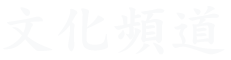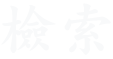我三次被劫持到廣州戒毒所迫害
同年12月26日,我在單位上班,幾個公安惡警、派出所的惡警,以我去北京為由再次強行將我綁架到戒毒所。在這期間,不法人員們想盡辦法迫我寫「三書」。如將我與吸毒、收教人員關在一起,20多人擠睡在一起,她們有生疥瘡的,淋病的。由於吃、睡、拉、做工都在倉中,倉裏粉塵滾滾,螞蟻、蟲子咬人奇痛奇癢。
戒毒所不法人員強迫我們看栽贓陷害法輪大法的宣傳片。有一次,強逼我寫「自焚」觀後感,我將「自焚」的部份破綻寫在紙上交上去,並在倉裏講真象。第二天,戒毒所一女副所長,為了證實我寫的情況,特意又放了那一段鏡頭,結果她發現我寫的是真的,輕輕搖了一下頭,倉裏的人員發現更多造假鏡頭了,大家都在議論紛紛。
由於巨額的經濟負擔,我丈夫不斷受到派出所、國安、單位的施壓,惡警既恐嚇又騙錢,妻子失去自由,兒子無人照顧等等原因。丈夫在巨壓、矛盾之中,被迫多次以婚姻關係想讓我表面放棄修煉。我被非法關押了半年,每天還勒索收費50元,國安一惡警還騙了我家人5千元。
2002年2月,我與另一同修在街上第三次遭非法綁架並送往戒毒所。這次我們不配合邪惡的任何要求,拒絕做工,絕食、絕水抗議關押迫害。
在絕食絕水四天後的一個晚上,國安惡警、戒毒所一副所長,把我騙到樓下辦公室,先是想讓我放棄絕食,見我毫不動心,就指使吸毒的男女人員,共不下十人,將我又拉、又推、又抬,強行放在醫務室的床上,有人按頭,有人按手,腳,旁邊還有站的,坐的,護士強行給我打針。由於我不停的掙扎,不停的講真象,和勸他們不要這樣迫害法輪功修煉者,並告訴他們善惡必報的天理,所以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在我的左腳面上打了一針。
在以後的幾天裏,不法人員們改用鼻插管灌食,在插管前,戒毒所一女副所長想從我口中灌食,我咬緊牙關,她就親自用一個醫用的鐵做的工具使勁撬我的牙齒,有的保安為了在她面前邀功,有的踩我手,有的踩我腳;我的頭也被他們按的動不了。
因為我一進倉就開始跟戒毒人員講真象,她們都明白了真象,所以他們從勞動地回來,看見我被插管的情景,都哭了,都吃不下飯。因為每天都有2名戒毒人員看著我,由於她們明白真象,在我每小時立掌發正念時,她們還幫我看著,有的還讓我煉動作給她看,我為她們明白真象而高興。
不法人員第一次插管迫害我時,我在她們不注意時把管拔了出來,後來他們插管就用膠布固定在我的鼻子上,用手銬銬著我雙手固定在水泥床上,強迫吸毒人員日夜看著我,不能站立,坐不能直腰,只能躺下一邊身,從灌食上銬後的幾天裏,我一直沒有大小便,但吸毒人員每天跟我洗臉,有時擦身。到了第九天的傍晚,國安惡警只好到戒毒所把我倆放了。
在這九天中,我不斷的向戒毒所的所長、指導員、管教、醫生、護士、戒毒人員說明真象。明白真象的都有意迴避參與對我的迫害,那個指使給我打針的副所長有一天還小聲跟我說:這次不關我的事(指灌食),看來他也害怕遭惡報了。
我一出戒毒所的大門,就看見父親和大法弟子,他們把我直接接到他們家。這時我知道丈夫因無法承受牽連、分居的痛苦,已向法院提出離婚。簽字後,他跟我說610要判我勞教,他單位用我兒子的就業對他恐嚇。我聽後當天就離開了我工作、生活的地方,離開了親朋好友,獨自漂泊在外。同年5月底,惡警把那位同修綁架到了槎頭勞教所迫害。
2002年9月中秋節前一天,我也被不法人員們在異地綁架到了槎頭勞教所三大隊。我被關在小房子裏,惡警還派了一個「夾控」(勞教人員)監視,強逼我背所規,不准睡覺。我堅決抵制。後來不法人員把我調到另一間報紙房,該房子的窗戶都用報紙糊住了,改換2個「夾控」日夜輪班折磨我,不讓睡,不讓坐,不准動,面向用報紙封住的窗戶日夜站立。
當時真的是度日如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出現了噁心嘔吐現象。因我已絕食幾天,吐不出東西來,第五天晚上,全身疼痛,我剛動一動,一「夾控」就揮拳打我,一「夾控」用指甲捏我的手臂,我的雙腳早已腫得走路不便了,我提出驗傷,無人理會。兩個「夾控」,一個天天迫我寫「三書」,一個天天罵我,我最心痛的就是她罵大法。由於惡警、「幫教」的恐嚇、引誘、欺騙和折磨,加上我自身的執著,被邪惡鑽了空子,給自己的修煉留下了污點。但當我清醒過來時,我開始做我應該做的事:背師父的大法、發正念,向同修說明任何轉化都是錯的,還讓同修有機會就寫作廢聲明。
在我將離開槎頭勞教所前,我讓同修將我親手寫的「嚴正聲明」帶出去上網,嚴正聲明在勞教所裏寫的、講的任何不符合大法的東西作廢;同時在每日給惡警看的日記中聲明自己在這裏時所講、所寫的任何不符合大法的言論、文字作廢,並拒絕惡警安排我在春節聯歡會的表演。由於我當時心態很正,惡警們沒有一個來找我麻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