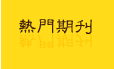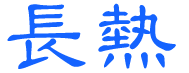小說連載:醒(二)
夜更深了,玉潔望著母親的像,心裏想,誰能想到,歷史是這麼快地重複著,人們竟是這樣健忘,文革才結束了二十年,一場迫害人民的運動又出現了。也難怪,和文革相比,這場運動顯得更詭秘,更狡猾,讓人不易察覺,利用了人們的自私和對金錢的慾望,激發了那些惡人的貪婪和獸性。其實,玉潔現在還不知道,這場迫害的殘酷程度竟也是歷史上罕有的。
玉潔很為婆婆慶幸,因為在他們走後不久,全國上下開始了揭批法輪功。一夜之間,好像甚麼都顛倒了。婆婆隔三岔五地打過越洋電話來,囑咐他們不要相信報紙、電視上的宣傳,並說劉慶的哥哥一家也開始煉法輪功了。後來,隨著風聲越來越緊,當婆婆再說這些時,劉慶在一旁就打斷了,媽呀,您說點別的不成嗎?您那邊甚麼都不怕,我們可還想過日子呢。玉潔很懂得婆婆的心情,安慰婆婆說,我們都知道,也不是小孩子了。但是婆婆還是希望劉慶能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玉潔內心苦笑,她太了解丈夫了,除了掙錢,他還能幹甚麼呢,那滴水不進的心田,沒有甚麼可以打動的了。
暑假過後,玉潔接了初一年級的班主任,玉潔所在學校是一所普通中學,學生都是被一流重點中學刷下來的。開學的第一天,新生中一個有著與年齡不符的憂鬱眼神的男生,引起了她的注意。現在的孩子,不論家裏有錢沒錢,都被慣得不像樣,用同行老師們的話說,是一茬不如一茬。但這個叫劉宣的男生,他的成熟讓玉潔吃驚,開學的第一天通常都很忙,收費、領書、領校服……,劉宣竟然默默地在幫忙,玉潔憑著直覺,就任命了他當班長,玉潔注意到,有幾個學生因此而交頭接耳,表情異樣。玉潔沒有在意,每屆學生都這樣,他們來自同一所小學,互相了解,可能有矛盾,慢慢就習慣了。誰知,這次下課後,竟有學生來向她打小彙報,說劉宣的父母都是煉法輪功的,他母親還被勞教了,不應該選他當班長,過去他在小學裏一直是大隊長,後來由於父母問題,加之學習成績突然下降,就被撤銷了。玉潔恍然大悟,那眼神,那種憂慮,多麼熟悉,二十多年前的她也是這樣。
玉潔沒有做出撤銷劉宣班長職務的決定,原因來自那眼神。後來,實踐證明,劉宣確實能幹,學習出色得令所有老師喜歡,因為在這樣的普通中學,能碰到一個一點就透的聰明學生不容易,而且劉宣正直、善良、懂事,沒有獨生子女身上的驕氣和霸氣。
由於文革時的經歷,也由於劉宣的優秀,玉潔格外地照顧他,鼓勵他,不想讓他受到任何的刺激。但玉潔發現,她的照顧有點多餘,因為在劉宣憂鬱的眼神中,玉潔也看到了當年她所沒有的勇敢,他並不怕別人說他,有個學生私下向玉潔告狀,劉宣有時散布法輪功的理論,告訴同學們法輪大法好。
玉潔一直想找劉宣談談,但每次都欲言又止,怕他受刺激。劉宣好像幾次也有話要對她說。玉潔注意到,每次學校廣播裏要求班主任組織班會,批判X教組織,劉宣就緊張地看著玉潔,而每次玉潔在廣播結束,都沒提這個主題,每每這時,劉宣都是目光閃閃地興奮地看著她。玉潔對此很開心,有一種能保護別人的滿足感。
當終於有了和劉宣長談的機會,玉潔還沒來得及問甚麼,劉宣竟搶著說,「王老師,我真為您高興。」
「為我高興?」
「在這場邪惡的迫害中,您擺正了自己的位置,沒有同流合污」。
「邪惡的迫害?擺正位置?甚麼意思啊,我還以為你要謝謝我呢。」
「嗯,我是要謝謝您經常幫助我。」劉宣有些窘態,好像覺得自己說話太急了。
「我在文革中受過苦,知道你的心情,放心,有我在別人不會欺負你,如果誰歧視你,你告訴我,我找他。」
「我?沒關係。我不怕。」劉宣的眼光清澈得可愛。
「真的?那你為甚麼總是顯得那麼憂鬱。家裏怎麼樣了,常去看你的母親嗎?」 玉潔問。
劉宣沉默了一下,終於說,「有時去。」他眼光轉向一邊,玉潔發現,那表情竟是大人才有的悲憤。
玉潔發現自己並不是很了解他,一個十三歲的孩子。
「聽說,你在小學一直學習很好,上重點中學絕對沒問題的,怎麼快升中學了,學習成績突然下降了?」
劉宣一下臉紅了,半天才慢慢說,「我的父母一直沒有放棄修煉法輪功,媽媽到北京上訪被拘留,放出來後,街道、派出所經常去家裏騷擾,那些警察,進門就翻箱倒櫃,還說要再抓爸爸媽媽。當時我確實很害怕,怕他們都被抓走。每天上課,心不在焉,一下學就往家跑,推門看媽媽還在不在,要在家,才放心,所以,學習一天比一天差。」劉宣說到這,才發現,不知甚麼時候,王老師已經轉身背對著他,向窗外望去。
他接著說:「後來媽媽真的又被抓走了,爸爸也被迫離開了家,我被送到奶奶家。有一段時間,我很想他們,整天哭。後來,原來那些一塊煉功的叔叔阿姨,經常在我放學的路上跟我聊天,他們說,我媽媽很偉大,做的是一件最偉大最神聖的事。」
「偉大?」含淚的玉潔從沒想過這個問題,這年月還有誰能稱得起偉大。
「你剛才說的邪惡迫害是怎麼回事?」玉潔停頓了一會兒才問。
「老師,您知道嗎?江澤民為了搞垮我們,給法輪功造了很多的謠,現在所有電視、報紙上關於法輪功的都不是真的。江澤民還偷偷地下令對法輪功要『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對抓到的法輪功學員要『往死裏打,打死算自殺』。 所以,您在廣播電視聽到關於法輪功學員自殺、跳樓的消息,很多都是這種情況,法輪功從92年開始傳,99年以前的七年時間裏,怎麼沒有這種自殺、走火入魔的情況,在外國也有很多人煉法輪功,我看過照片,還有外國人呢。他們造了太多的謠言,老師您可不要相信他們。
「那你的媽媽怎麼樣?她也……?」。玉潔略微遲疑地問。
「只聽說媽媽被打得……打得……很慘。」劉宣低下頭,玉潔還是看見了那閃爍的淚光,她輕輕拍了拍劉宣的肩膀,半晌才問:「勞教所是允許接見的,你經常去看她嗎?」
「沒能見到她,因為……,因為她不肯寫悔過書,那裏的管教不讓見,」劉宣略微抬起了頭,眼睛看著牆,玉潔從他的濕潤的眼睛裏竟看出了自豪。
「悔過書?!」玉潔想起了電視上那些痛哭流涕的「法輪功練習者」。「不寫悔過書就不讓見親屬,還要挨打?」
「嗯。而且……,而且……」,玉潔又看到了那眼中的悲憤。「要想見媽媽,我必須……,必須要罵我的師父……,我不罵,他們就不讓我見媽媽……」,劉宣終於忍不住趴在桌上哭起來,肩膀劇烈地抽動著。
玉潔回到家,已經七點多了。推開門,看見劉慶懶懶地躺在沙發上,豆豆在一邊做功課。
「這麼晚呀,我說吧,你這個班主任就別幹了,明兒我再請你們校長吃飯,跟他說說。咱家也不缺你那點班主任費,弄得早出晚歸的,那麼辛苦幹甚麼。呦,你今天怎麼啦?誰又惹你生氣了?」
玉潔說,「我今天心情是不太好,這麼晚了,我們出去吃飯吧,我不想做飯了,而且,我有事跟你商量。」 劉慶聽了這話,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起來,高興地說,「豁,頭一次聽說,你主動提出出去吃飯,你總是省吃儉用的。我不跟你說了嗎,咱家錢花不完。」
飯桌上,玉潔看著劉慶,又望著豆豆,欲言又止。但是,還是憋不住,對劉慶說:「我想管你借一萬塊錢」。
「幹甚麼用錢,我給你買就是了,還說借。」
「我有一個學生,很可憐,我想幫他。」
「幫甚麼,要用一萬塊,太誇張了吧?」
「他爸媽是煉法輪功的,媽媽被關在勞教所,他想見他媽一面都不讓,我想花點錢,找人通融通融,讓他們母子常見見面……,」
劉慶眼睛大大的,「嘿,我說你,淨來這嚇人的,好好的,又和政治扯上邊。」
「甚麼政治呀,經過文化大革命,你還不明白,『黨說你是啥,你就是啥……。』像豆豆的奶奶那樣的,怎麼會反政府?她煉法輪功以後,連活魚都不吃了,怎麼會自焚?豆豆煉功後,再沒得過病,這你也知道。你們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文革給我的刺激太大了,我不相信那一套。老百姓鍛煉鍛煉身體,就值得酷刑鎮壓?你知道嗎,我學生的媽媽在勞教所裏,被他們往死裏打。」
「挨打?有這事,電視裏說是『和風細雨,耐心細緻的思想教育』。」
「共產黨有甚麼真話?我學生不能見他媽媽,要想見還要罵人。甚麼世道,比文革還厲害。」
劉慶沉默半晌,說「共產黨確實甚麼都幹得出來,咱還是過咱們的安穩日子,別惹這些事,快吃吧。」
玉潔有些失望,衝動地拉著劉慶的手,「你就幫我一次,我很少求你辦事,幫我找人去問一問,不就是花點錢的事嗎,這是她的情況,都在這張紙上了。」
豆豆也在旁邊說,「爸爸,你就幫幫忙吧!」
劉慶看了看妻子和女兒,順手把紙條塞進兜裏,說了句:「可不一定是錢的問題,到時候你可要承受得起。」說著埋頭吃起飯來。
半個月過去了,劉慶也沒有動靜。玉潔心裏暗暗著急。終於,有一天,劉慶下班回來,進門就抱怨,「真沒想到,天下還有這麼黑的地方」。
「怎麼了?」玉潔問。「這回是工商局還是稅務局的?」
「哪兒啊,勞教所!」劉慶幾乎在喊了。「現在,這世道簡直是明搶了,就為讓親屬見個面,這是國家法律允許的嘛,要這麼多錢。」原來,劉慶在玉潔說了的第二天就找人到勞教所打聽,回話說,劉宣的母親是死硬分子,不悔過,要辦成事得多給錢,劉慶馬上送了五千塊錢過去,但幾天也沒信兒,後來再找人一打聽,說是給少了,劉慶又給了五千,還沒動靜,劉慶有些不耐煩,找來朋友問,到底他們要多少,朋友說了實話,像劉宣媽媽這樣的,給多少都不多,乾脆死了心吧。劉慶自己也覺得這事辦的窩囊,也沒敢告訴玉潔,事就這麼拖著。誰知今天一上班,朋友打來電話,說事辦的有門了,勞教所說再給三萬塊錢,就立刻安排他們母子見面。
「三萬塊,太多了吧,一萬五成不成。」劉慶習慣地砍了價,不知為甚麼話一出口,心裏竟有些後悔。誰知,對方很快來電話還了價,兩萬塊不能再少。劉慶很快拿了錢送過去,這次勞教所還真馬上安排了第二天的會面時間。想著那年幼的孩子能很快見到母親,想著玉潔會高興地跳起來,劉慶心裏竟有一種多年沒有的興奮感覺。
果真,玉潔不僅跳了起來,還樂得拉著劉慶轉了幾圈。玉潔馬上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劉宣,劉慶在一旁聽著、感受著他們的快樂。
第二天,玉潔上班,看見劉宣空出來的座位,心裏喜滋滋的,連學生都看出來了,老師今天心情好。下班一路走著,玉潔想,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給劉宣打電話。遠遠地看見家門口,一個熟悉的身影。
「劉宣,你來啦,怎麼樣……,你怎麼啦!」玉潔看見劉宣紅腫的眼睛,眼神呆呆的,轉身的姿勢竟都有些僵硬。玉潔趕快開了門,把劉宣扶到沙發上,給他倒了杯水。
「你媽媽怎麼樣?」玉潔看見劉宣的已經乾澀了的眼裏滲出了越來越多的淚水,大滴大滴地流著,由於過度的刺激,他的身體還是僵硬的,他緩緩地說:
「他們叫我去,就為利用我逼我媽放棄修煉,他們當著我的面,用膠木棒打媽媽,用電棒電,媽媽沒有屈服,我忍著,不哭……,可是……,可是……。」
劉慶接到玉潔帶著哭音兒的電話,匆匆趕回了家。一進家,屋裏黑黑的,只有廚房亮著燈,玉潔在做飯。這時的劉宣已經平靜下來了,正和豆豆在屋裏打坐。玉潔示意劉慶別出聲,拉著劉慶到廚房,把事情經過仔細說了。劉慶沒有說話,轉身出了廚房,他斜靠在沙發上,久久地望著昏暗中劉宣打坐的身影。
飯桌上,大家都默默地吃飯,劉宣吃得很慢,好像每咽一口飯,都費很大勁兒,但他為了不讓玉潔著急,他還是一口接一口地吃著。劉慶為了緩和氣氛,打開了電視。
電視上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臉龐,大家都愣住了。那是劉宣!劉宣在悲慟地哭著,兩個警察站在他的身後,像是在安慰劉宣的樣子,接著畫面又出現了劉宣的媽媽和爸爸的照片,畫外音說,「……他們不顧家庭……」。
「那是今天上午,他們偷拍的!」劉宣的眼淚又下來了。
「顛倒黑白!」玉潔喊起來了。「他們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這樣……無恥。」
劉慶眉頭緊鎖,看著玉潔氣得一會兒站,一會兒坐,沒有說話。
飯後,劉慶開車送劉宣回家。
路上劉慶一直沒有說話。到了劉宣家樓下,劉慶停了車,他轉過臉對著劉宣:「我一直想問你……,煉法輪功就真那麼重要嗎,為甚麼不能退一退,表面說個不煉。」
劉宣望著劉慶:「叔叔,為甚麼好的不能說出來?對就是對的,正的為甚麼偏要說成是邪的呢?」
劉慶半晌不語,看著劉宣那雖然紅腫,但清澈如水的眼神,劉慶內心竟然有一絲自慚形穢的感覺,朦朧之間他突然覺得這個眼神曾經見過,光明磊落、坦蕩真誠。
劉慶目送著劉宣進到了樓裏,他轉身回車裏,拿出手機,撥通了朋友的電話,「問問勞教所,給多少錢他們能給辦個保外就醫,這回他們一口價,我不回價。」
劉慶說完,發動了汽車,準備回家。這時,一個人影飄然而至,輕輕地敲著車窗。
劉慶搖下車窗,一愣,在哪見過。「你……」。
「我是劉宣的父親劉凱歌,我能進來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