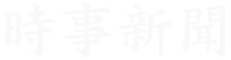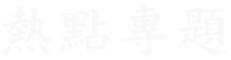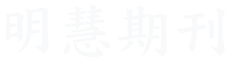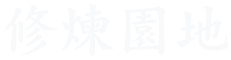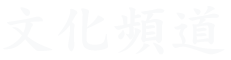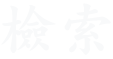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裏(下)
「我始終不敢相信一個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善良群體,一個只為做好人,對國家和社會有百益而無一害的群眾性活動,會遭到殘酷的打壓和迫害。可它卻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並且還在繼續發生著。我曾四次遭邪黨綁架,非法關押長達二十一年半,期間受盡了非人的折磨,酷刑的摧殘,人格的侮辱。當我回憶過往的慘烈時,原本在邪惡面前不曾掉過眼淚的我,卻忍不住一次次的淚如泉湧。」
| ──作者的話 |
(接前文)
(四)電視插播真相 遭二十年冤獄折磨
成功走脫後,我和同修取得了聯繫,找到了大法資料點,和資料點的同修一起做資料,刻錄光碟,投入助師正法、救人的洪流中。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十八日兩天,我成功參與了法輪大法真相視頻的插播。我們兩人一組分別在青海省西寧市、青海省民和縣、甘肅省蘭州市紅古區、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甘肅省慶陽市慶城縣等七處成功插播了真相視頻。還有其它幾處,由於插播方法沒有掌握好,沒有插播成功。
在慶陽市西峰區的插播,由於地點比較隱蔽,惡人一直沒有找到插播點,我們的視頻又是循環播放的。氣急敗壞之下,惡人竟然下令停電三天。
我們選擇在邪黨「十六大」召開前夕,魔頭將要下台之際,又是在晚上七點黃金時間段播出的。一時間,驚動了邪黨中央、公安部,派出了所謂的專家參與了非法搜捕,僅廣武門一帶,就布控了二百多警力。我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再次遭到邪黨綁架。惡警魏東等將我拳打腳踢後,塞入車內,拉到了雁灘。他們給我戴了兩副背銬(一副銬在手腕處,一副銬在胳膊彎處),然後提著背銬,將我拎到了七樓蘭州市公安局一處。
1、酷刑逼供
何波、魏東等惡警把我鎖在了「老虎凳」上,把手腳卡在「老虎凳」的卡子裏不能動彈,又在我的頭上扣上頭盔,上身用皮帶綁在「老虎凳」的靠背上,整個身體不能動彈。他們不斷擰緊卡在我手腕處的螺絲扣。就這樣,每隔四、五分鐘,就再緊一次螺絲,整個夜晚都是在不停地緊螺絲。我疼的撕心裂肺,渾身顫抖,大小便失禁,幾近休克。
天亮後,他們把我送到西果園看守所。沒過多長時間,又從西果園看守所轉到華林坪蘭州市第二看守所。後來,他們又多次非法審訊,都是徹夜在「老虎凳」上度過的。
記得有一次,他們把我鎖在「老虎凳」上,上緊螺絲後,他們就在一旁吃飯、打牌。這時來了一個警察,拿了一根木棍,形式上表現很兇,拿著木棍使勁往螺絲上捅,嘴裏還吼著,卻是往反的方向捅,在松螺絲扣,同時也想把螺絲搗壞。搗了一會,他見螺絲鬆動了,便起身走了。
過了很長時間,何波見我沒動靜,過來看螺絲鬆動了。嘴上罵著:我們這裏出了奸細了。又說:他們不願幹得罪人的事,這樣的事情都讓我們幹了,月底還一樣的和我們拿獎金。
至此,我知道蘭州市公安局一處有許多明白真相的警察不願聽從邪黨的指揮,跟隨他們同流合污迫害大法弟子。心中由衷地感謝剛才為我松螺絲的警察,他冒著危險,為大法弟子解難,將來一定會得到善報的。
這時的何波幾近瘋狂,他拼命的緊螺絲,我的身體一陣陣的戰慄,牙齒也不停的磕碰,幾近崩潰。之後,我的手腕麻木了一年多時間。
2、多次被禁閉
第一次禁閉:手銬和二十多斤的新鑄腳鐐
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年後,二零零三年九月,邪黨人員又將我劫持到蘭州監獄。在入監的第一天,由於不配合他們的搜查,制止他們對其他大法學員的打罵,我和慶陽的同修劉志榮(後在天水監獄遭迫害去世)被關入禁閉室。
禁閉室是一個只有三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是一個二平方米的全封閉式的小院,禁閉室裏有一磚石結構、凹凸不平的石床,床的前槽是一個解大小便的坑,屋內無任何取暖設施,每間屋關三、四人,床上睡一、二人,側槽睡一人,前槽睡一人,被關禁閉的人都不准帶被褥,只能和衣躺在地上。吃飯不給筷子和勺子,只能用手抓著吃。
他們在搜查我攜帶的衣物時,惡警趙之勇將我穿的一件夾克衫故意撕破,他是想找裏面是否藏有大法資料。我穿的褲子也弄的找不見了。惡人給劉志榮戴上六十四斤重的腳鐐,手銬和腳鐐用鐵絲串在了一起。我被戴上二十多斤重的新鑄成的腳鐐,手銬和腳鐐也被用鐵絲串在了一起。由於是新鐐,上面還有毛刺沒有打磨掉,一不小心腳腕就被刺破了,疼痛難忍。我用新發的他們強行給我們穿上的「囚」服的褲腿將鐐環捲住包起來,這樣毛刺就不會直接刺到腳腕了,也就不那麼痛了。最後,那條褲子的褲腿被刮磨的稀爛。就這樣,我被非法禁閉了一個月。
第二次禁閉:手銬和六十四斤的腳鐐
第二次禁閉是在一年後的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臨近冬至前,監獄管理科考核邪惡的「行為規範」時,因為我不配合他們的考核,與一副科長發生爭執,管理科原維斌過來,拍我的頭部,我以手擋之,之後他們又從我身上非法搜出大法師父的經文。以此為藉口,給我加戴上六十四斤重的腳鐐,且用鐵絲與手銬串在一起。
這是一個新建的禁閉室,進入禁閉室的大院,進入走廊,便到了禁閉室。這是一個五平米的小屋,靠牆是一個水泥板床,床的前頭是一個水沖式的便池,便池的上方是一個封閉式的窗戶,窗戶的旁邊是一個小鐵門,門外是個二平方米的全封閉式的放風場。整個禁閉室和放風場有安裝攝像頭,呈全方位無死角監控。禁閉室有地暖,但凡是有被關進禁閉室的,這個禁閉室的暖氣便停供。每個禁閉室的門外走廊裏有一個控制該禁閉室暖氣的閥門。
進入冬至,又下了一場雪,我的下身只穿了一條線褲,腳上一雙「回力」牌球鞋,上身穿一件長袖夾襖。每天早上六點,便把我放在放風場裏,由於腳鐐沉重,我在原地一坐就是一天,挪不了地方,晚上九點才收回禁閉室,每天都要在零下七、八度的低溫下挨過,溫度最低時達到零下十一、二度,寒風凜冽,凍的我瑟瑟發抖。
禁閉室有一邪惡的「事務犯」,經常到放風場用手指彈我的眼睛。由於手、腳都被固定死,無法迴避,所以他往往得逞。晚上九點,把我收回禁閉室後,戴的腳鐐,就只能在禁閉室的側槽和衣躺下。由於腳鐐過重,又是和手銬串在一起,身體是蜷在一起的。一晚上只能翻兩次身,天就亮了。
非法審訊時,由兩名包夾犯人架著我的胳膊,我用雙手抓住腳鐐,他們把我抬進審訊室。主管獄警的副監獄長石天佑曾幾次向禁閉室的警察問過我的情況,他們想用這種辦法使我屈服,而最終氣得石天佑暴跳,也未能得逞。他們怕把我凍死,禁閉一個月時把我放了出來。卸下腳鐐時,我已經不能走路。
「事務犯」是蘭州監獄專有的名詞,就是幫助警察處理日常工作事務的犯人,每個監區都有,一般都在「管教辦」做事。而以教育科、衛生所、管理科禁閉室、入監隊為多,這些人都是通過關係賄賂進去的。蘭州監獄有個潛規則,進教育科、衛生所、管理科禁閉室五萬元,進入監隊、老病殘監區三萬元。每年的節假日還要送禮、進貢。所以,每逢監獄長換任,這些科室和監區的犯人都要進行一次大的清理、整頓。清理出來後,再把自己的關係戶安排進去。主管獄警的副監獄長換任,會有一次比較小的調整。所以蘭州監獄有一個怪現象,老病殘監區75%─80%的人是頭腦靈活、四肢健全、身體健康的人,而每個生產大隊早上出工的病號隊排了一長溜,有攙著扶著的,有坐輪椅的,有拄著拐杖的,各式各樣,應有盡有。這也成了蘭州監獄的一道邪惡景觀。
第三次禁閉:強行轉化
第三次禁閉是二零零五年九月,蘭州監獄要求強行「轉化」所有的法輪功學員,為此,他們給我加戴手銬,我不從,丁輝等警察把我壓倒在沙發上,強行給我戴手銬,我的頭撞在了暖氣片上,血流如注,縫了九針,才止住了傷口。
他們把我關了一段時間禁閉之後,又由監區接回,把我鎖在三監區的小號室裏,由王國華、薛玉生等犯人四人包夾,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各種邪惡的襲擾不斷。後來聽到從新橋監獄(對外叫「康泰」醫院)回來的病犯講,王國華得了一種怪病,死在了新橋監獄。
國內國際善良人的幫助
在蘭州監獄被非法關押的十八年裏,也一直都有善良人幫助我,資助我,他們和我一起吃飯,資助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日用品,曾有幾個被教導員叫去以不減刑相要挾強行拆散。也有不懼邪惡的,就和教導員說:我們在一起只是吃個飯。甚至在我的頭被撞破後,他公開指責邪警的粗魯、野蠻。就是在邪惡對大法弟子打壓最嚴重時,獄警規定任何人不得和我說話、接觸,還有一些善良人在家人來餐見時,將打包帶回的菜各樣給我撥一份,放在飯盒裏,放到暖氣上,然後以身體碰我,以手指暖氣上的飯盒後,迅速走開。這樣的善良人在三監區、十監區都有。
一次,在十監區,我和教導員發生了爭執,圍觀的犯人很多,但沒有一個藉機對我動手的,若在一般情況下,早有犯人為討好教導員,從背後就下了手了。也有善良的警察從獄外給我帶進來烤紅薯、酸奶等,他們的善舉也在時時感動著我,鼓勵著我。還有的警察與我談到我出獄後的生活打算,也在時時關心著我。
更有來自港、澳、台、海外及大陸同修對我的加持和鼓勵。同修給我寄來的各種郵件,有明信片,有信件,還有匯款,裝了滿滿一塑料筐。由於邪惡的封鎖,我雖未見到過一封,但我知道這些郵件,那是同修對我的鼓勵和加持,同時也在震懾著邪惡,使邪惡不敢對我肆意妄為。
還有獄中的同修,通過各種方式,在生活上接濟我,在言行上鼓勵著我。我能夠在如此邪惡瘋狂的打壓中,如此漫長的巨難與迫害中走到今天,全仰承慈悲偉大師尊的加持與保護,是大法的威德,有同修的鼓勵,還有善良的世人對我的幫助,與我自己內心對無限敬仰的師父與大法始終如一的堅定信守。
3、多次蹲小號
在蘭州監獄的十八年,邪惡為了不使我和其他大法學員接觸,大部份時間把我和其他同修隔開,單獨關在一個監區。二零零六年從三監區轉來的大法學員多了,惡警又把我轉到了十監區,在十監區邪惡又開始了對我迫害。
一次性被關小號三個月
蘭州監獄有十大惡警,十監區就佔了兩個──教導員戴學義、大隊長高振東。尤其是戴學義,一肚子壞水,壞點子層出不窮。記得是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剛過,惡警戴學義把我關進了小號,由殺人犯牛明泉、搶劫犯谷寧寧等四個包夾,將我吊起掛在高鋪的床架子上兩個星期,不准睡覺,致使我全身浮腫,雙腳,腿腕處呈黑紫色,失去了知覺,尿液呈紅色,意識處於半昏迷狀態。一次,我要小解,他們打開手銬將我放下,我竟一頭栽倒,把馬桶碰翻,尿液洒了一地。
還有一次,殺人犯牛明泉用拳頭猛擊我的腹部,致使我疼痛難忍,額頭上的汗都滲出來了。就這樣,在小號室渡過了漫長艱難的三個月。
教導員戴學義迫害過許多大法弟子,事隔不久,便得了肺癌死了,遭了報應。
高振東也迫害過許多大法弟子,平涼大法弟子曹璽就曾被他吊在鐵絲上,腳尖幾乎離地。他的報應遲早會到。
金吉林被折磨的生不如死
大法弟子金吉林在第一次被劫持到蘭州監獄時,在九監區遭到原副教導員張海軍的殘酷迫害。他暗示包夾犯人用開水燙金吉林,起水泡後,又用大頭針刺破洒上食鹽,不准金吉林睡覺,持續的迫害致使金吉林痛苦難忍,最後以熱水瓶內膽的碎片將自己的動脈割斷(編者註﹕這是在中共殘酷迫害下,承受不住的極端行為,不是法輪大法的原則真、善、忍所倡導的,是法輪大法法理禁止的),險些失去生命。在第二次被劫持到蘭州監獄後,金吉林遭到來自七監區大隊長魏周江的迫害。二零二一年八月,我出獄時,金吉林還在小號遭受迫害。
王有江在獄中被迫害致死
大法弟子王有江,在五監區遭到原大隊長張海軍、原教導員王國臣的殘酷迫害,致使王有江中風後出現偏癱,失去了生命。
孫照海牙齒被打落的所剩無幾
黑龍江佳木斯市大法弟子孫照海,在一監區遭到原大隊長王國臣、原教導員孔繁平的持續迫害。惡人把孫照海關進小號,綁在「死人床」上,給孫照海上「老虎凳」。惡人把孫照海的牙齒打落的所剩無幾,都沒能打垮孫照海對大法的堅定意志。在經歷了半年多絕食、絕水反迫害後,經過了近一年小號室的迫害,惡人發現動搖不了孫照海,解除了關小號。
二監區劫持一白銀市平川區大法弟子,年已七十,我走出蘭州監獄時,他被關進小號,已經四個多月沒讓睡覺了。希望國內外相關組織與同修給予關注。
再次被關小號:黑頭套 老虎凳
惡人每隔不長時間便要製造出一些事端,藉此來打壓迫害大法學員。有次收工,惡人藉口我沒有按照他的口令要求做,把我叫出來,要單獨訓練,我抵制邪惡的迫害,站著不動。
這時,副教導員張玉泉過來,再次把我關入了小號。他和監區長王子卓兩個沆瀣一氣,把我銬在了上鋪的床架子上,晚上不讓我睡覺,出工時,給套上黑頭套,到了生產車間,便鎖在「老虎凳」上,同時還準備了束縛帶(監獄自制的,用編織袋的料縫以粘貼的粘條,束縛人的胳膊,腿、手、腳用的)、透明膠帶(惡人怕我叫喊,而準備纏嘴用的)、擔架之類的刑具,由吳國華、張正舉等四人包夾,邪惡之勢兇猛。
由於長時間的吊掛使我的意識出現模糊,身體也出現水腫。昏迷中,我想起師尊的教誨:「大覺不畏苦 意志金剛鑄 生死無執著 坦蕩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
惡人強加給我的十幾年艱難的牢獄生活我都走過來了,在這最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還過不去嗎?都能過去,一定能過去。就在這堅定的一念作用下,在師尊的加持和大法的保護下,我終於從險惡的迫害中走過來了。
疫情期間,獄警分為兩班,一個星期一輪班,警力明顯不足,又到了下半年,生產上他們想要衝刺一下,拿個第一,多發點年終獎,所以不願投入更多的人力,便把我從床架子上放了下來。
緊接著,又發生了職務犯冉鴻舉病死在蘭州監獄。冉鴻舉的死,又牽出一件獄內重新犯罪的案子。王子卓急於「滅火」,便放鬆了對我的迫害,我又從小號回到了監舍。
三、蘭州監獄的「形像工程」和奴工生產
1、財政費用於「勞改積極分子」和「一類犯」
自從張永維從天水監獄調到蘭州監獄任監獄長以來,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大搞「形像工程」。他把財政撥給蘭州監獄犯人的伙食費都用到了給所謂的「勞改積極分子」和「一類犯」改善伙食上去了。然後,用拍照、上報紙、上電視宣傳等方式,提升他個人的形像,而其他犯人的伙食平時是見不到豬肉的,只有到過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才能吃上一、二頓豬肉。
2、整卡車的清油不知去向
平時每週三、四頓的改善只能吃到切的很碎,肉眼很難找見的雞胸脯肉,因為沒有油、炒出來的菜經常出現糊鍋現象。而整卡車的清油從犯人食堂拉出不知去向。他們把從市場剔剩下的雞架骨買來,和土豆炒在一起做的菜,硬說成「紅燒雞塊」,把切成碎末的雞胸脯肉和菜炒在一起,說成是某菜炒肉,而菜只有土豆、蓮花菜、芹菜、胡蘿蔔等最廉價的三、四種蔬菜,而張貼的菜譜卻是五花八門、營養豐富,以此來欺騙犯人的家屬。
3、奴工生產任務逐年上漲
而犯人做「奴工」的生產任務卻逐年上漲。第一年,他剛到蘭州監獄,給各監區下達的生產任務就翻了一倍。第二年,又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以後逐年上漲,且幅度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早上六點半出工,一直到晚上六點半收工,中午有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這還屬於正常出收工。若是加班,要到晚上八點半或九點。完不成任務,還要遭電擊,橡膠棒抽打,更有甚者冬天給戴上手銬抱電桿,夏天在太陽底下暴曬,用盡各種手法。
4、無條件沒收個人基本生活用品
蘭州監獄不給配發內衣、內褲、棉被、棉褥等生活用品,而入監時帶到監獄的又不讓穿、用。每次監獄檢查、清理出去的衣服,被褥,垃圾場上堆積如山,有些是剛從監獄超市購買的,卻不准穿、用。監獄超市曾出售過收音機、線衣、線褲、棉衣、棉鞋、球鞋等物品,後來都成了「違禁品」,一律收繳,無條件沒收,一副流氓、強盜、無賴的嘴臉。
我的兩部收音機、兩副耳機,還有衣服、鞋、皮帶、茶杯等被搶走,卻不給任何說法。暖氣差到了極點,監舍樓又是四面透風,根本起不到保暖作用。暖氣晚上十一點多,準時停供,早上六點,才開始供暖。晚上蓋兩床被、褥,還被凍的醒來多次,而監獄就只允許每人有一床被、褥。
5、死後的搶救擺拍
犯人生病了,一般是得不到及時治療的。二零二零年一年,蘭州監獄犯人由於生病得不到治療,病死的多達二十多人。十監區從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死了三人,兩人死在了監獄,一人送到新橋監獄(「康泰」醫院)不到一週便死了。如此草菅人命卻沒有人過問;王星雲是患「膽管結石」不給醫治,活活疼死的。直到臨死的那一天,他還在跟著大隊出工,由兩人扶著走,晚上收工回監舍,死在了監舍裏。郗星武是患胃癌不給醫治,直到癌細胞擴散,送到「康泰」醫院,不到一週便死了。冉鴻舉患心臟病,多日不給治療,等他不行的時候,才開出外診單,送「康泰」醫院準備「治療」,可未等出監獄大門,人就死了。
蘭州監獄形成一個欺世盜名的罪惡慣例,就是在人死了之後,才給死者掛上吊針,插上氧氣,擺出一副經過搶救無效死亡的假相,或掛上吊針,插上氧氣,送上車往「康泰」醫院拉的樣子,其實人早已死了。
冉鴻舉的死還牽出一樁獄內重新犯罪的大案。
6、冉鴻舉之死 牽出的獄內五十萬詐騙案
據說,冉鴻舉生前是酒鋼公司財務總監,有筆不合法的費用領導讓其做了,後來事發,以挪用公款罪,判了冉鴻舉有期徒刑,冉鴻舉心裏不服。後來他遇到職業騙子龔積德,龔積德假說可以找到好的律師,幫他打贏這場官司,律師費要五十萬。冉鴻舉信以為真,先期通過冉鴻舉的家屬付給龔積德姐姐十五萬。
可是事後,冉鴻舉一直沒有見到律師的面。冉鴻舉感到有些蹊蹺,找到龔積德,龔積德推說律師正在審理他的案子,還差三十五萬元未付,付後,律師就會接見他,冉鴻舉已經感到有些上當,但還是在積極籌措另外的三十五萬元。在見不到律師的情況下,冉鴻舉急火攻心,導致心臟病復發,死在了蘭州監獄。
在冉鴻舉的家屬來處理遺體時,家屬還誤以為是監獄在幫助找律師,便拿出收條,提出人已經死了,官司也就不用打了,要索回先期支付的十五萬。至此龔積德獄內詐騙案暴露出來。監區長王子卓緊急聯繫龔積德的姐姐,索要回了十五萬,算「滅了災火」。
可不曾想,二零二一年,來了個司法大檢查,最高檢工作組進駐蘭州監獄一個月。雖然王子卓早有準備,在車間的會議室安裝了竊聽器,還把舉報箱裏的舉報信讓值夜班的犯人掏了個乾淨,可還是有犯人通過最高檢的檢察官約見的方式舉報了此案。龔積德被關進禁閉室等待法律的審判。
但這件事卻並非這麼簡單,試想十五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誰又能輕易將十五萬交給一個陌生人呢?沒有龔積德和冉鴻舉多次和家人聯繫,是促不成此事的,而多次打電話,只有警察能夠提供這樣的方便,那麼他們之間又存在怎樣的利益關係呢?值得深思。而就是這樣的監獄,竟被省監獄局樹立為「先進單位」。這樣的監區年年被評為「先進監區」,王子卓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眼前的一切使我無語,我不知道甚麼樣的邪惡體制,才能演繹出如此荒誕的劇情。
結語
在被非法關押的二十一年半的時間裏,我經歷了被單位開除公職,我在林家莊的房子被拆,房子裏的家具不知去向。我曾去派出所報案,但派出所不予受理;我居住的晏家坪的房子,由於水、電、暖、氣改造時,我被非法關押在蘭州監獄,未能得到改造,只得從鄰居家拉電接水,由於鄰居早有想佔據我房子的想法,便趁火打劫,對我停水斷電,目前只得在外租住,妻子在巨大的壓力下被迫與我離婚,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被拆散,本來可以領到二十二個月的失業救濟金,蘭州市社保局卻重重刁難,不予申領,低保也無著落。
而這一切的遭遇,只是因為我對真、善、忍大法的信仰,對法輪大法的堅守,為使世人擺脫欺世的謊言,明白大法真相,從而得到佛法的救度。
在此我奉勸蘭州監獄張永維、張海軍、王國臣、孔繁平、王子卓等人,因為你們是深受邪黨妖言蠱惑的迷中人,希望你們趕快清醒吧,別再做違背天理,違背良心的事,別再為邪黨賣命,充當迫害大法弟子的千古罪人,善惡到頭終有報。為了你和家人的未來,停止迫害,將功贖罪,才有可能得救,才會有未來。
(全文完)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4/3/13/2161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