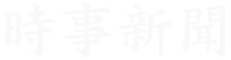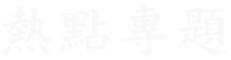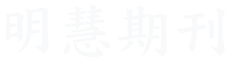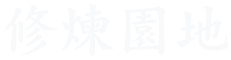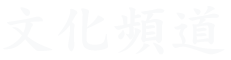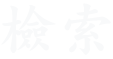大陸法會|正信堅如磐石 大法威力展現(一)
值此第二十屆明慧網大陸法會之際,我向師尊彙報一下自己的修煉心得。
一、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持實修、維護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惡黨發動了對法輪大法的迫害。我去北京上訪,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在北京,我經歷了多次危險,都在師尊的保護下成功走脫。我悟到,要讓更多的同修走出來上訪,我就回來和同修們交流,希望他們走出來。後來我被人構陷,被非法勞教兩年。
非法關押我的勞教所是一個惡名昭著的邪惡黑窩,在那裏死人是常有的事。到了勞教所,我和另外兩位同修被關在一個房間。當天下午,一位同修提議,我們通過一起煉功的方式維護大法,我也同意了。因為剛經歷了看守所的嚴重迫害,我心裏留下了陰影。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對同修說:「你們先煉吧,我以後再煉。」那兩位同修沒有受我的影響,立即開始煉功。他們很快就被警察銬起來,帶走了。
同修走後,我越想越不對勁:這兩位同修不正是師父安排來幫助我的嗎?我為甚麼到關鍵時刻就退縮了呢?這不是怕心造成的嗎?怕心不也是執著嗎?我想到了師父說:「整個人的修煉過程就是不斷的去人的執著心的過程。」(《轉法輪》)
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去掉怕心。否則,怎麼能維護大法、證實大法?可是在如此邪惡恐怖的環境下,想要去掉怕心,談何容易?我一次一次鼓起勇氣,卻又一次一次放棄。十多天後,我終於打定主意,就在當晚煉功。可我發現晚上舍房值夜班的是一個打人非常兇狠的小組長,我又放棄了。
又過了十多天,我再一次決定就在晚上煉功。可我發現,雖然舍房內當班的不是那個很兇的小組長,可舍房外走道上值班的那個大組長更凶殘。我心想,如果落到他手裏,不知道會被打成甚麼樣。我又一次打了退堂鼓。過後,我心裏很是懊悔、自責、沮喪,那種想要突破卻突破不了的煎熬,別提多難受了。我想到師父說「做到是修」(《洪吟》〈實修〉),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到。
又經過半個多月的煎熬,怕心和正念的反覆拉鋸,正念終於佔據了上風。我把心一橫,無論將遭受甚麼樣的迫害,就是被打死我也一定要煉功。我決定晚上煉靜功。
晚上我從鋪上坐起來,發現值班的那個很兇的小組長居然睡著了。我打手印時,心怦怦的跳,身子在微微發抖。打完手印後,我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平靜下來。外面走廊上來來往往的人看見了我煉功,但就像沒看見一樣。我就這樣靜靜的煉了大約一個小時,終於被小組長發現了。他一邊罵著,一邊拿起一個木凳朝我砸來。事後,我感到無比的輕鬆,我為自己終於衝破了怕心的束縛而高興。這次去怕心的經歷,給我以後反迫害、證實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後我決定了:要去做證實大法的事的時候,要義無反顧,說做就做。我沒有了先前的膽膽突突,拖泥帶水。
在整訓隊三個月後,我被安排當衛生員。這個崗位輕鬆,沒有生產任務,又受犯人尊敬,是不少人花錢找關係都難以得到的。我想:我如果在這裏舒舒服服的把兩年非法勞教期混滿,那不是虛度光陰嗎?我是修煉人,無論在甚麼環境,都不能忘了修煉和證實大法。我打算把牆報上誣蔑大法的內容清理掉。當我走到牆報前準備動手時,發現他們已經更換了內容。我決定換另一種方式證實法。我上一次煉功是晚上在室內煉的,這一次我要大白天在公開場合煉。
那一天,剛好是星期天,整個大隊幾百個犯人都沒有出工。我爬上一個高台,開始煉功。我剛開始煉,就聽見有人喊:「有人在煉法輪功!」緊接著有人慌慌張張的喊:「快去報告管教!」幾百個犯人看著我煉功,我一點沒有害怕。我雙目微閉,從第一套開始,一心不亂的煉功。當煉到第三套功法時,一個警察輕輕的拉住我的手,說:「我看你煉了這麼一陣,感覺法輪功沒甚麼不好呀!」警察說完,只是把我銬起來,沒有打我。
儘管我因為公開煉功失去了衛生員的崗位,但我一點都不後悔。大法弟子證實大法是理所當然的,我不是來求安逸、圖享受的。
不久,我看到同修被警察毆打,我大聲制止。警察惱羞成怒,把我關了十五天禁閉室。禁閉室環境非常惡劣,當時正值冬天,氣候非常寒冷。禁閉室裏所謂的床就是一個一米左右寬的水泥台。前兩天,每天只給我吃兩頓飯,而且份量很少,一頓只有二兩左右。警察為了凍我,只讓我穿很薄的衣服。前兩天沒給我被子,第三天才給我丟進來一床很薄的被子,蓋和沒蓋一樣。
我想到師父說:「修煉就得在這魔難中修煉」(《轉法輪》)。我想:「這不正是修煉提高的好機會嗎?我以往忙於上班,哪有這麼多的時間,哪有這麼清靜的環境?」我決定好好利用這段時間,紮紮實實的修煉提高。我每天抓緊時間煉功、背法。背一陣法,煉一陣功,交替進行,不知不覺一天就過去了。儘管我睡很少的覺,還是感覺時間不夠用。我會背的法不多,我就一遍一遍的反覆背《洪吟》、《精進要旨》、《轉法輪》中記得的內容。
我以前練其它氣功的時候,雙盤很輕鬆而且盤腿不痛,腿很靈活。沒想到修煉大法後,腿突然變的僵硬了。別說雙盤,就是單盤都很困難,翹的老高不說,還疼的厲害。我悟到,其它功法是修副元神,法輪大法是修煉主元神,所以就得明明白白的吃苦。我業力大也是一個原因,既然業力大,就要消業,就要能夠吃苦。
我一直想要突破雙盤,現在有這麼充裕的時間,這不正是好機會嗎?我採取循序漸進的辦法,一點一點延長時間。由於看不到時間,我就把一段法或者一首《洪吟》背十遍作為一分鐘。我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不論怎麼痛,不到時間絕不放下來。我堅持到預設的時間後,並不滿足於此,常常是給自己一個「獎勵」──再堅持十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因為劇烈疼痛,我不停的流汗,先是上衣濕了,後來褲子也濕了,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別人冷的受不了,我卻感覺不到冷。很快,我就突破到能雙盤一個多小時了。
幾天後,我決定不再計時,從吃完早飯後一直盤腿,直到中午飯送來才放下來,兩頓飯之間大約四個小時。剛盤上一會兒,腿就開始痛,逐漸的越來越痛,然後發展到全身每一處都在痛,那種痛簡直無法形容。我想到了師父說:「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轉法輪》)。我就一直堅持著,不管怎麼痛,就是不拿下來。到後來,我痛的直流淚,很想放聲大哭,卻不能哭出聲。淚水和汗水一齊往下流著,時間也在巨痛中一秒一秒的延伸著。終於熬到了開飯的時間,我才把腳拿下來。我從鋪上艱難的滾到地上,再忍著劇痛爬到門前,顫顫巍巍的把碗遞過去打飯。然後我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躺了一個多小時,才緩過勁兒來開始吃飯,這時飯早已涼透了。
儘管我吃了很大的苦,但所有的付出沒有白費,我從單盤都很吃力,一下子突破到能盤腿好幾個小時。同時,我感到另外空間的本體昇華很快。幾天後,我在煉「佛展千手法」時,剛念完口訣「身神合一,動靜隨機」(《大圓滿法》〈二、動作圖解〉),我一下子感覺到「身」和「神」真的溶合在了一起,體會到了在我所在境界中身神合一的內涵。那種感覺非常美妙,卻又無法言表。
我的身體改觀也很大,紅光滿面,精神飽滿,完全看不出是被關了禁閉的人。和我同時被關禁閉的一些人,穿的比我多,蓋的比我厚,禁閉期滿時,整個人面黃肌瘦、目光呆滯、精神恍惚。有了這次經歷,我的承受能力強了很多。
捆繩子,是監獄、勞教所最殘忍、最厲害的酷刑手段。犯人一提到捆繩子,都是談虎色變。其方法是用特製的棕繩,一圈一圈的捆在手臂上,從肩膀以下一直纏到手腕處,再使勁的拉緊繩子。繩子勒進肉裏,導致整個手臂血液不能循環,然後再把兩隻手反綁到背上。如果掌握不好力度和時間,很容易造成兩手殘廢。
捆繩子的時候痛的撕心裂肺,解開繩子的時候更是痛的無法形容。為甚麼用棕繩,而不用尼龍繩或者麻繩等繩子?因為棕繩非常粗糙,有毛刺,拉緊繩子時,能起到撕裂的效果。同時棕毛猶如針扎一樣,能最大成度的給人製造痛苦。
勞教所為了讓我放棄修煉,指使兩個警察把我按在地上,把我的手捆上棕繩。一邊一個警察,兩隻腳同時踩在我的一隻手上,使勁的拉緊繩子。我的手快速腫脹,腫起來的肉完全把繩子包住了,手也變綠了。儘管痛徹心扉,我還是一聲不吭,沒有一絲妥協的意思。
兩個警察又把我兩隻手反綁在背上,繩子由脖子往下在胸前交叉,然後在背上打了一個結。接著,用鋼管伸進繩子使勁絞。這在原來巨痛的基礎上,又給我施加了巨大的痛苦。警察惡狠狠的問:「還煉不煉法輪功?」儘管我已經痛到快要失去意識了,但我堅定而又平和的說:「我可以為法輪功獻身。」我說完後,警察都愣了。過了一會兒,警察才說:「看好時間。」時間雖然只有幾分鐘,但我感覺好漫長。
時間到了之後,他們解開繩子。鬆開繩子之後,我感覺像受到了強烈的電擊,又感覺同時被千萬根針在扎一樣。繩子上滿是勒下來的肉皮,整個手臂滿是繩子留下的毛刺扎在肉裏,我的整個手臂血肉模糊、皮開肉綻。
半個月之後,我的手臂開始結痂,一邊結痂一邊流黃水,疤痕十年後才完全消失。捆繩子之後的大半個月時間裏,我的兩隻手都沒有知覺,吃飯時筷子都拿不住,只能把嘴伸到碗裏。
過了不久,我和幾位同修被關進嚴管中隊。嚴管隊被稱為監獄中的監獄,長期挨餓,還要被迫每天跑步、走操等體罰。本來勞教所的伙食就差,嚴管隊就更差,而且份量很少。吃的菜大多都是菜農不要了的,餵豬可能豬都不愛吃。菜葉都枯黃了,而且長了很長的秸稈,秸稈切成一節一節的,嚼不爛,難以下咽,犯人們稱為「子彈殼」。菜裏面油很少,甚至菜湯上面漂浮著蟲子。即使這樣,份量還很少。早飯的饅頭小的像麻將牌一樣,稀飯是清湯寡水的,只有碗底才有一點飯粒。
再惡劣的環境,我們也沒有忘記大法弟子的責任。每當嚴管隊開會,只要警察的講話中有污衊大法的話,我們十多個同修就大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警察叫勞教犯捂住我們的嘴,可勞教犯只是做做樣子。有時他們還幫著我們一起喊,聲音有時比我們還大。
我有一個缺點:性格木訥,少言寡語。尤其在公共場合說話容易緊張,表達困難。曾經有一次,鎮上開會讓我發言,我本來是做足了準備,但到了台上時,卻漲紅了臉,憋了好幾分鐘愣是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後我在一片哄笑聲中尷尬的下了台。
我想:師父這麼好,法輪大法這麼好,我如果還是這麼木訥、不善言辭,怎麼澄清中共邪黨對師父和大法的抹黑造謠,讓世人認識法輪大法的美好?我決定在勞教所期間就克服這個缺點,將來出去後才能更好的證實大法,講清真相,助師正法。我把反映勞教所剋扣勞教人員伙食、虐待勞教人員作為突破口,既在實踐中磨煉我的表達能力,同時又反迫害。
我每天一有機會就反覆琢磨嚴管隊公布的伙食支出表,估算公布的數據和實際數據之間的差距。我發現,勞教所嚴重造假,大量經費被他們貪污剋扣。一天上午,我看見一個犯人挑著一擔長的很老的菜走進大門。我跑過去,一把抓住他挑的菜,然後把管伙食的司務長叫來,想讓他看看給我們買的是甚麼爛菜,然後再一筆一筆的算賬。可司務長來了之後,我腦袋卻一片空白,本來想好的話卻不知道怎麼說。司務長罵我神經病,把我打了一頓。我沒有氣餒,準備抓住機會,再次提高突破。
過了不久,我期待的機會終於來了。政協、人大、婦聯要組團到勞教所參觀。那天早上,我把饅頭留著沒吃,放在衣服口袋裏,準備以饅頭為實物,向參觀團揭露勞教所虐待勞教人員、貪污剋扣伙食費的惡行。當參觀人員都走進嚴管隊後,我對警察說:「我要去反映情況。」我也不管警察同不同意,說完就徑直向參觀的人群走去。警察慌了,為了阻止我向參觀團揭露勞教所的邪惡,他大聲的叫喊:「有犯人要哄監鬧事,有人要暴動。」參觀人員嚇壞了,一窩蜂的往外跑,慌不擇路之下甚至有人摔倒了。事後我才明白,根本不應該先給警察說,應該直接找參觀團揭露勞教所的惡行。
這次參觀是勞教所極為重視的一次活動,沒想到被我給捅了這麼大一個簍子,不但影響到評全國先進勞教所,而且當時有北京來的「610」高官正在勞教所蹲點。當時犯人和警察都認為我闖了大禍,後果很嚴重,不知道要遭受怎樣嚴酷的報復迫害。我想:「我有師父,我怕甚麼?」他們最凶殘的捆繩子迫害都已經使過了,還能有甚麼招數?大不了被打死而已,大法弟子是可以為宇宙真理付出生命在所不惜的。
晚上,中隊長把我找去談話。我說:「剋扣囚糧,從古到今都是大罪。你們給那麼少的飯,嚴重的摧殘了勞教人員的身體健康。每一個勞教人員進嚴管隊,前三天不給飯吃,後三天每天只吃一頓,再三天吃兩頓,第十天才吃三頓。每頓的飯菜不但質量很差,份量更是少的可憐。我想找他們反映情況。」中隊長說:「這是嚴管中隊,就是要嚴管,就是要這樣。」我說:「那誰給了你們剋扣伙食、虐待勞教人員的權力?請你把授權你們這樣做的文件拿出來。」他無言以對。
我又說:「我仔細分析了一下你們公布的每個月伙食收支表,財政撥給中隊的和中隊實際支出的至少相差一萬元。一個月一萬,一年就是十二萬元,這筆錢到哪裏去了?你能說清楚嗎?」中隊長心虛了。我一筆一筆的把賬算給他聽。這時候,在師尊的加持下,我頭腦清晰,有理有據,滔滔不絕。中隊長一直聽我講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說話。
我說:「為甚麼那些勞教犯被你們折磨的這麼慘,他們還是『二進宮』、『三進宮』,三番五次的進來?因為你們用惡的方式根本改變不了他們的內心,他們出去了還是要幹壞事。法輪功為甚麼能真正的改變人,讓人棄惡從善?因為法輪功用真、善、忍啟迪人的善念,讓人從內心深處認識到做人要向善,生命才有希望,所以很多以前有惡習或壞毛病的法輪功學員修煉後,都真正的改好了。」中隊長靜靜的聽我講著,最後他讓我回舍房睡覺。
原本以為會受到的各種迫害,煙消雲散了。犯人和同修都驚奇不已。出了這麼大的事,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這是勞教所幾十年從未有過的事。我知道,是因為我走正了,師父保護了我。
第二天早上,饅頭比平時大了很多,稀飯也稠了很多。勞教犯們既興奮又感激。他們見到同修,都笑瞇瞇的豎起大拇指,激動的說:「法輪功了不起,太偉大了。」是啊,除了偉大的法造就的大法弟子,誰還會冒著被殘酷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險站出來為別人發聲呢?
從此以後,我的表達能力和說話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在甚麼場合,不管對方甚麼身份,即使對方是高官或者專家教授,我都能侃侃而談,而且一直佔據主動。常常我簡單的幾句話,就能直擊要害並破除邪惡的迫害。如果讓我一直說,我能一口氣說上幾個小時,而且思路清晰,說話在理,邏輯性強。多次針對我的迫害,因為我的「能說會道」而沒有被迫害成。我的嘴成了我清除邪惡、破除迫害的利劍;喚醒世人、救度眾生的利器。經常有人說我知識淵博,以為我是高學歷的專家、教授,其實我只不過是初中文化,是法輪大法開啟了我的智慧。
二、正念破除迫害
從勞教所回家的第二天,和我比較熟的年輕警察小孟(化名)來了,說找我到鎮政府說幾句話。我剛走下樓,就被強行塞進警車,拉到市「610」辦的洗腦班。當地政府派了兩個人做包夾,其中一個是混社會的混混,人很兇,平時天不怕地不怕的。
這是一個很邪惡的洗腦班,中共邪黨投入了大量資金,戒備森嚴。這裏所有參與迫害的人不但補貼高,而且伙食好,每天菜不重樣。全市很多同修都在這裏被迫害過。因為有在勞教所去怕心打下的基礎,我心裏一點不害怕。我堅信師父說的「一正壓百邪」(《轉法輪》)。
到洗腦班的第二天,來了一個市裏所謂的「轉化」專家。他說:「隔壁的某某都轉化了,你也應該轉化。」我說:「『轉化』嘛,是個好事情。」他一聽,高興壞了。我接著說:「但是『轉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邪的向正的轉化,惡的向善的轉化,壞的向好的轉化。你說對不對?你們是不是本著這個原則做的?如果不是,那你們就是在犯罪!」我說完後,他落荒而逃。從此後,他再也不敢到我的房間來了。後來又有幾個企圖「轉化」我的人都相繼敗下陣來。包夾笑話他們,說:「你們還想『轉化』他,看樣子你們要被他『轉化』。」
他們說不過我,就給我放誣蔑大法的錄像。我說:「既然這個班是為我辦的,就要以我為主,這房間的一切都要為我所用,我想看甚麼就看甚麼。你們既然把這叫法制學習班,那就看法制頻道。」我把電視遙控板拿過來選台,恰好中央台的《今日說法》欄目正在講一個非法拘禁的案子。我馬上給他們普法。我說:「我是一個沒有任何違法行為的公民,你們把我綁架到這裏,就是私設監獄、非法拘禁。你們是在違法犯罪。」儘管他們中有法學碩士,但都啞口無言。
洗腦班每天晚上都要開會,商量怎麼迫害大法弟子。我這個房間的頭每天晚上都去開會,向上級彙報我的情況,同時傳達迫害指令。我對他說:「你每天去開的甚麼會?回來一點也不說。你要搞清楚主次,你們現在吃的這麼好、工資這麼高,全是因為我你們才能享受這麼好的待遇。你們吃我的、用我的,還不讓我去開會。從明天開始,你不要去開會了,讓我去開!」
他們見不但「轉化」不了我,還經常被我弄的灰頭土臉的,於是他們就想把我再次弄進勞教所。他們把我叫進一個房間,一個警察坐在桌子後面,旁邊站著兩個魁梧的警察。我一看這架勢,一下子就明白他們是想問一個筆錄後,就把我非法關進勞教所。
警察問我叫甚麼名字、甚麼性別、出生年月等。我知道他們知道我叫甚麼名字,但我不能配合他們。我靈機一動,說:「你們連我名字都不知道,就把我抓來關起,太不像話了。我走了。」說完就往外走。在走廊上,我大聲說道:「難道我們煉法輪功的就低人一等嗎?就可以隨便抓來關起嗎?」幾個警察追過來,故意說我喊法輪功口號「法輪大法好」,想要打我,被我正念制止了。
我對那個比較兇的包夾說:「你是個有膽量、不怕事的人,也是有正義感的好人。今天這事你也看到了,他們想加害我,就隨意捏造事實。萬一他們把我整出個三長兩短,恐怕會連累你。」他聽了後,正義良知被激發出來了。這個包夾走到辦公室,把桌子猛的一拍,大聲說:「今天這事我在場,確實是你們不對。你們把他關了十多天,竟然還不曉得他叫甚麼名字,還想打他。我給你們說,人是我們帶來的,你們這樣亂整,萬一整出事了,我要找你們。我看你們也沒甚麼本事『轉化』他,我們把人帶回去算了。」
就這樣,我又回到了縣裏。縣「610」知道「轉化」不了我,就把我單獨關在一間屋子裏,派人把守著我,也不再搞甚麼「轉化」了。
一年後,我的身體出現了病業狀態,警察把我送到醫院。我對醫生和護士講:「我是煉法輪功的,本來身體好好的,是他們把我非法關起來迫害,才導致我身體出問題的。他們隨意私設監獄,現在又把醫院病房搞成監獄。你們趕快把你們醫院的保安叫來,把他們抓了。」我對警察說:「你們如果非要給我動手術,萬一出了問題你們誰來負責?你們誰敢打保票不出問題,那就請他立下字據,出了問題我就找他。」他們誰也不敢出面保證,只有讓我回家。回家後,我身體很快就恢復了正常。
(待續)
(明慧網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3/11/7/2127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