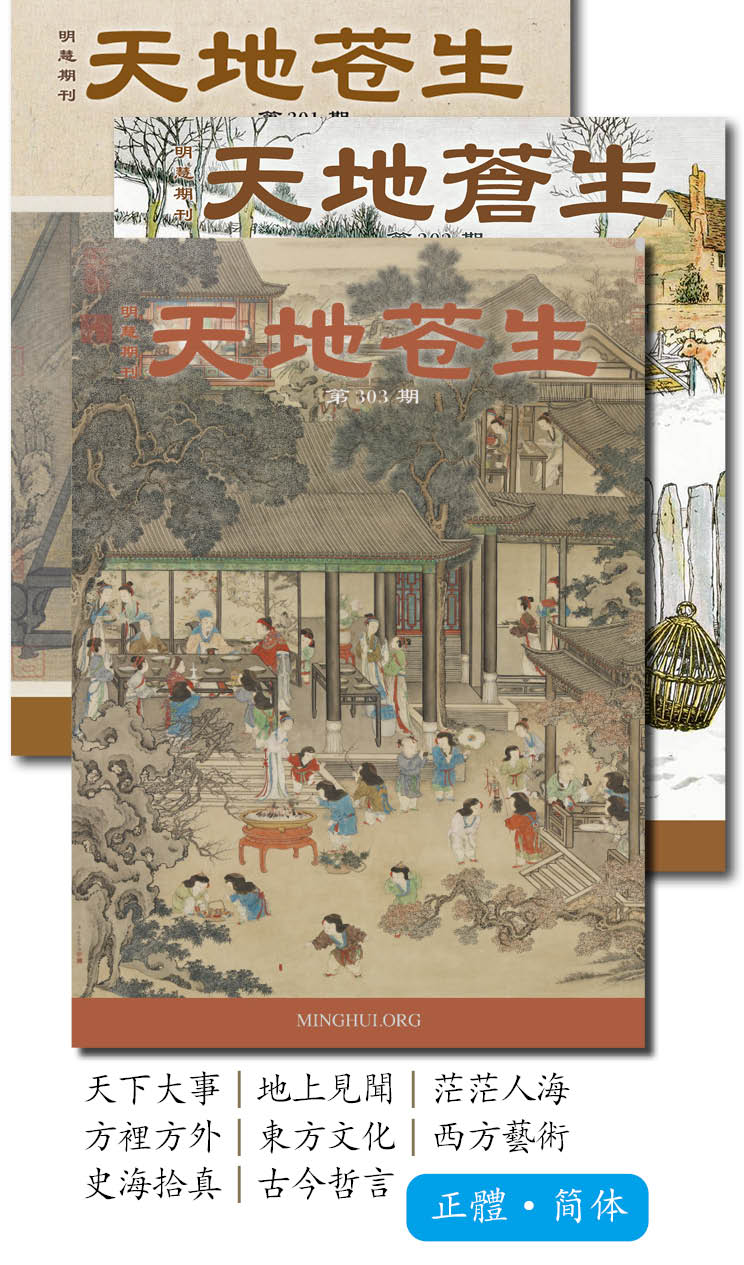靜心學法才能看到新的法理
從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停止打吊瓶後,又打止痛小針到四月底。在這期間,父親一直誦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父親的身體漸漸不太疼痛了。但是,父親仍然躺在床上,需要人整天護理。
這種情況對於我學法和煉功都有干擾,我用發正念清除干擾,效果不大。到端午節前夕,我靜下來向內找,才意識到干擾只是外因,而內因是我在學法、煉功和發正念都是走形式,都是在完成任務。
這時,我想起同修曾講過的一件事:這位同修的丈夫是煤礦工人,由於煤礦好幾個月沒開工資了,家中就沒有米下鍋了。同修把該幹的活幹完了,就盤上腿認真的學法。她丈夫看見了說,你真行啊,中午都沒飯吃了,你能有心情學進去嗎?而她卻說,越是艱難的情況下,越要認真的靜心學法,因為想的再多也沒有用。說完,她繼續學法。她丈夫急的在屋裏屋外團團轉。
同修把一講法學完後,對丈夫說,你趕快去礦上開支吧。她丈夫說,絕不可能。同修說,我告訴你了,你愛去不去。丈夫聽後,騎上摩托就去了。到了煤礦,領導就說,你來的正好,聽說你家沒米下鍋了,先把你的工資開了,解決你家的燃眉之急。丈夫樂顛顛的拿著工資回家了。其他礦工聽說此事,也趕緊去開支,可到了煤礦,那個開支的人已經走了。
以上故事讓我明白了,護理好父親和學好法的關係不矛盾,首先安排好父親的生活順序,白天給父親放大法弟子的歌曲聽,並且告訴父親堅持誠念九字真言,然後做到靜心學法、煉功。開始時,很難做到,但是在用心堅持和發正念的情況下,漸漸就好多了。
靜心學法後,能夠破除人的觀念和經驗。例如,我家住四單元,有一天在二單元和六單元都安了攝像頭。有同修來我家後,對我說,你用棍子把攝像頭往上頂一頂,它就照不到了。
同修走後,師父的一段法在我腦中顯現出來:「對煉功人講,人的意念指揮著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為一個常人來講,意念指揮著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1]因此我沒用人的方法去動它,就想它那個東西不管用,也不好使。
到第三天,來了兩個人,把攝像頭給拆掉了,正好我經過時看到,還有個老頭兒問那兩人,為甚麼要拆掉啊?其中一人氣呼呼的說,告訴我們安裝完就給錢,可是去取錢,就推三推四的不給,拆掉了,免得惹氣。
在此前,我對「放下生死」的法理有些不明白,原因是只重視「死」字,沒重視「生」字。有一天讀到「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2]時,我眼前一亮,知道了放下生死,主要是先放下「生」。常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與物質都是為「生」而用的,死而無用,唯有德和業死後才可帶走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走入大法修煉的,還沒怎麼學法煉功,迫害就發生了。別說去北京證實法呀,就是在家裏,怕的也不知如何是好,特別是「天安門自焚」偽案播出後,家裏人用各種手段和方式逼迫我放棄信仰,甚至以離婚來威脅。
而我冷靜的思考後,決定堅持修煉。那時候,我地有同修被綁架,家人也很怕的,最後說,你要堅持修煉,就出去躲一躲吧,我也只好同意了。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我就去了一個山區農場的親戚家裏,在那裏採野菜、刨藥材和採蘑菇等。開始時,還能夠堅持學法和煉功,但慢慢的就屬那種帶修不修的狀態了。就在這跑山的過程中,我把這個農場的三十多個連隊和幾個林場的位置和路線掌握的清清楚楚。
在二零零四年的秋後,我回到了家中,參加了學法小組,並參與了揭露當地迫害的項目。年底,《九評共產黨》發表了,我地同修都很精進,在二零零六年年底,我地基本發放完一遍《九評》。
也是這時,我聯繫上了我所去的那個農場的同修,得知,她那裏,除場部發了少量的《九評》,其它地方基本是空白區。我與同修切磋結果是,她出錢和小冊子,由我們租車和出《九評》。但他們沒人配合我們去發放,這樣,我就成了「嚮導」。我自制了地圖,標明位置、路線和里程,由我地的三位同修配合,把這個農場各個單位全部發了一遍《九評》和小冊子。
寫出這段歷程,我想說,在我們跌倒的時候,在脫離整體的時候,不要趴在那兒,要找機會奮起直追,師父會給我們彌補的機會的,只要我們去抓住這個機會。
在此,我也想和那些在「清零」和「敲門」迫害以及其它方面沒過去關的同修切磋一下,關沒過去,或沒過好,不要背包袱,更不要脫離整體和同修,更不要想師父要不要我了,此想法和行為正是舊勢力和邪惡想要的。此時,應該靜下心來認真的回頭看一看,沒過去關的原因是甚麼?執著的東西是甚麼?多學法,向內找,然後修去它,把心性提高上來,這是從根本上不承認舊勢力迫害,而不是嘴上說說。
我們每個同修都應該是在干擾與關難當中修出來的,我想這些關難都應該是我們提高層次的大好機會。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無存 〉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2/10/17/2043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