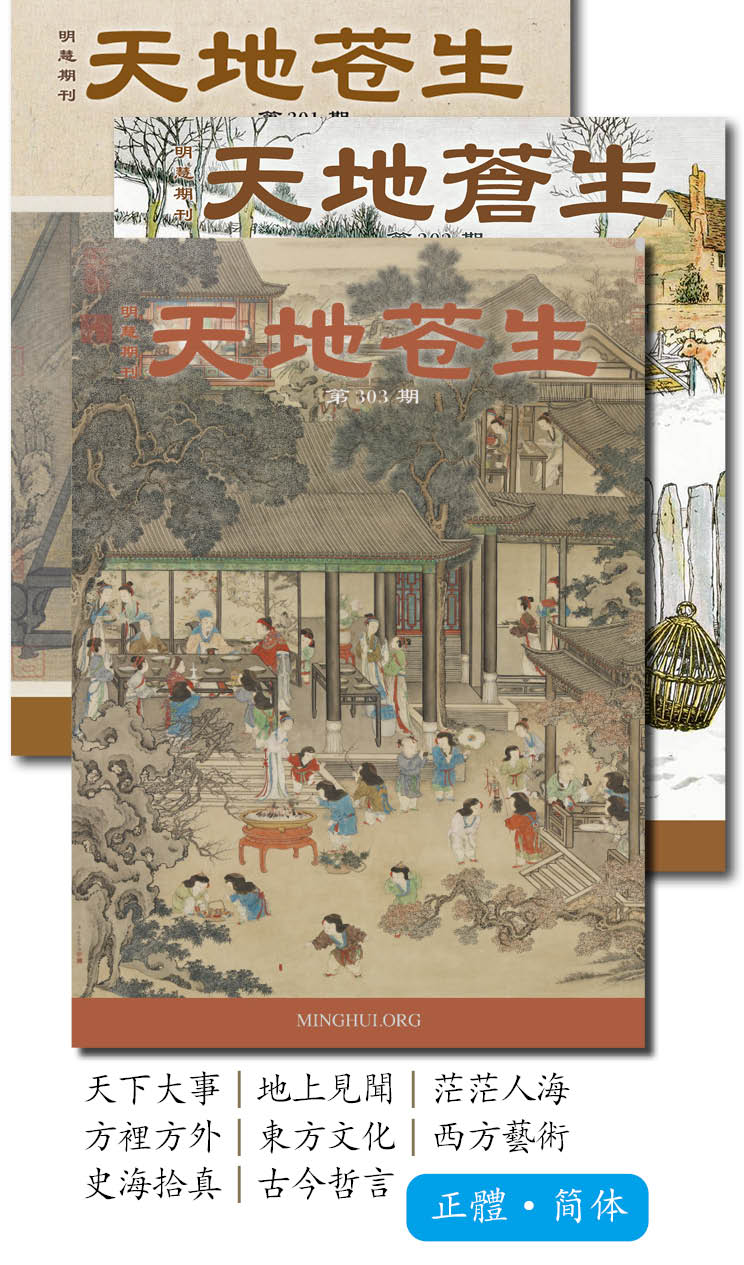煉法輪功獲新生 江西省教師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
今年六十八歲的童正英女士通過修煉法輪功,獲得身體的健康和道德的昇華。可是一九九九年之後,她多次被江澤民集團迫害,曾被非法勞教。
以下是童正英女士在訴狀中陳述的事實與理由:
1、修煉前疾病纏身
一九六五年我進入高安中學讀高一,接著就訂婚了,從此我有了思想包袱,而疾病也就纏身了。畢業時我因結婚不能考大學,只得在師生們的惋惜聲中痛苦地離開了學校,回到了娘家──華林下觀村。
在娘家我拖著病體教起了民辦。其實那時候我就有關節炎、支氣管炎、甲狀腺腫瘤、心臟病、頭痛、頭暈(一分鐘都未好過)、天天流鼻血等病。生了兩個孩子後,又增加了許多病:腰痛、神經官能症、拉血、吐血,還有婦科病。
由於疾病多我特別怕冷,渾身一點勁也沒有。如夏天生產隊長要我帶學生去收割稻子時就會說:「你只要在那裏指揮就行,你有病,不要做,因為你不去我們指揮不動。」
在炎熱的夏天,別人站在太陽底下都會汗流浹背,而我在太陽底下不但沒有一點汗,而且上身要穿四件褂子、下身要穿三條褲子,夏天天天如此,少一件都不行,多少年沒流過一滴汗。
在讀高中時,我的衣服都是同學洗,空手跟著她們去洗衣服還常常摔跤。在生產隊時,隊長七十多歲的岳母去出工都要挑東西,而我是唯一免挑擔的人,可空手去田裏作一點點輕活也常摔跤。
我怕冷到了不能吹一絲風和下一點冷水的地步。夏天叔伯們在我家門前(我父母給我作的房子)乘涼,等他們一走,我就從房裏出去關大門,就在關門時吹那麼一絲風,就要一夜咳到天亮,下一點冷水也一樣會咳個不停,所以我和小孩的衣服都是母親或妹妹洗,包產到戶後我五個人(四個小孩和我)的田地和我父母、弟妹們的在一起,我也沒去做過一次事。
後來病情越來越嚴重,頭髮變白了,耳鳴眼花,耳朵似乎越來越聾,神經越來越錯亂。天天見面的鄰居都不認識了,吃飯常常是拿著空碗坐到飯桌邊發呆,不知道去幹甚麼……
食慾也沒有了,無論母親弄甚麼好吃的菜給我吃,我都不想去吃,一聽說吃飯就噁心。我一年有半年大便時要拉血,而且量很多,看著拉出的鮮血,我常常淚流滿面。
為了治好我的病,母親、表哥、表嫂、表姐常帶我去看病,從本地到縣城、從本省到外省的醫院都看了,有時一天看幾個醫生,省城、縣城是經常去的。中藥、西藥、草藥、偏方不知吃了多少,可一點都沒用。
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收入在全村是最多的,可每年都因給我治病而用光,而且我爸爸每天收晚工後(除大雨、大雪天)都要到山上去砍一擔硬柴賣,當然這錢主要還是用來為我治病,村裏許多人背地裏都議論:「童老師的父母不知欠她幾輩子的債,這世總會還清了吧。」
父母看我越來越不行了,在我快滿三十歲時偷偷的為我製作了一副棺材。有人勸我去考民辦師範,我不去,因為以前保送的大學都沒讀成還去考甚麼民師呢,反正人都不知道哪天會突然死去。
可在八三年的暑假中學教導主任說:「這個老師去年都考得到,今年我給她報名,她不去考行嗎?」當中學會計通知我去複習考試的時候,我剛在人民醫院做過大手術又加上與結紮一次進行,一聽到這消息,我傷心得哭了好久。但為了報答他,我只得去考,結果還真考上了民辦師範學校。
考上了這個學校,就意味著自己成了公辦教師,工作有了保障。這樣我的身體也好了一點,但體重只有七十四斤。
八五年,我調到了村前中學任教語文。在那裏工作任務重,家務事多,除了不弄飯,作園子、打豬草、洗衣服等等基本都是我的事。當然,這些事很多時候有同事和學生幫做。不管怎樣,做事時總免不了下水,所以咳嗽從未離開過我。我感到身體又恢復了原樣。
我的頭除了暈和痛之外還有一種像要裂開似的感覺。漸漸地胸膛、腹腔都痛,我懷疑內臟全壞了,但是我又不敢去檢查。其實醫院就在學校正對面,看病很方便,只要兩毛錢掛號就行。可是我向來常常是身無分文,所以很少看病,也不想看病,也不想活了。
一九九七年暑假,一個福州軍區醫院的軍醫一看見我就說我得了肝硬化腹水的病,並且說我的眼睛看不清東西了。確實如此,我真的連自己的備課筆記都看不清了。但我還是沒去治療。
2、修煉法輪大法後無病一身輕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我到村前的法輪功煉功點一位同修那裏借了一本法輪大法的著作到家裏來讀。我讀了兩遍,覺得很好。接著我就用本子抄了下來送給了我遠在三十多里外渾身是病的妹妹。
從妹妹家回來後,我發現我的頭不暈不痛了,手、腳、腰、胸腔、腹腔都不痛了,後來發現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飛了,身體完全好了,比我得病前的身體還好了。我走路生風,精力充沛。我身體舒服,心也暢快,臉上整天都掛著笑容,嘴裏不停地哼著歌兒,因為我享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幸福。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體重增到了一百斤。我的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決心用真善忍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言行,學好法提高心性,做個師父要求的更好的人。
3、修煉後我沒有敵人
修煉後,我變得更寬容、真誠、善良了。我師父說修煉的人沒有敵人,我捫心自問,發現自己真的沒有敵人了。我把攻擊我的人都當作親人,產生矛盾了就找自己哪裏沒做好。有同事心目中我是個好人。
九九年上半年文教局要各中學評一個師德模範交上去,學校就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了。
二零零二年正月,學校幾個老師在高安街上碰到我,有一個老師說:「童老師,我們給你拜年來了,你們煉法輪功的個個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學校其他老師也都是這麼認為的。
4、江澤民所犯罪行
其實在九九年五月就常有地區、縣、縣各局和鄉級的領導找過我談話,要我放棄信仰。並且還罰了我們家一千多元錢。
九九年七月又有文教局的人到我校來逼我放棄修煉,否則就帶走我,這樣學校領導要我丈夫寫了一個不學不煉的保證,這個人才放過了我。
九九年八月份,文教局又辦了一個「學習班」逼迫所有修煉法輪功的人放棄信仰。
受江迫害以來我進了三次看守所和一次勞教所。
為了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二零零零年底我和三個老年同修去北京上訪,去說幾句真話:李洪志師父是好的,法輪大法是好的,修煉法輪功沒有錯。
可是我們剛上廣場,還沒來得及說甚麼,就被惡警推上了車,晚上送到了密雲縣。一到那裏就聽到車上打電話說:「貨到了,快來接貨。」這時我才明白,原來法輪功修煉者在他們心目中不是人。
第二天我們單位和鄉政府各派了一個領導去接我,到高安後他們直接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那裏一共呆了一百零五天。從看守所出來又進了縣民兵訓練基地的轉化班,在那裏縣、局領導逼迫每個同修轉化,有一個女同修被逼瘋了。
第二次是二零零二年的夏季的一天,我和家鄉的兩個同修去東方紅廖猴英同修處學發豆芽,無故又被東方紅鄉政府和派出所的人綁架到看守所關了三天,他們一見到我們就打,還說要打死我們,說別處也有人打死了煉法輪功的。
第三次是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九日晚,我和一女同修到楊圩去發真相資料(以前從未發過)被惡人舉報後,當地派出所的人把我們綁架到派出所,將我們用銬子銬著,第二天我們又被送進了看守所,這次又在看守所呆了一個月。
八月十九日,我們又被送到了江西省的一個女子戒毒所,實際就是勞教所。我們勞教的時間是兩年。
看守所、勞教所都不是人呆的地方,吃的是豬狗食(現在的豬狗根本不會吃這樣的食),幹的是奴工活,沒有自由、沒有安全保障、空氣沉悶得使人喘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