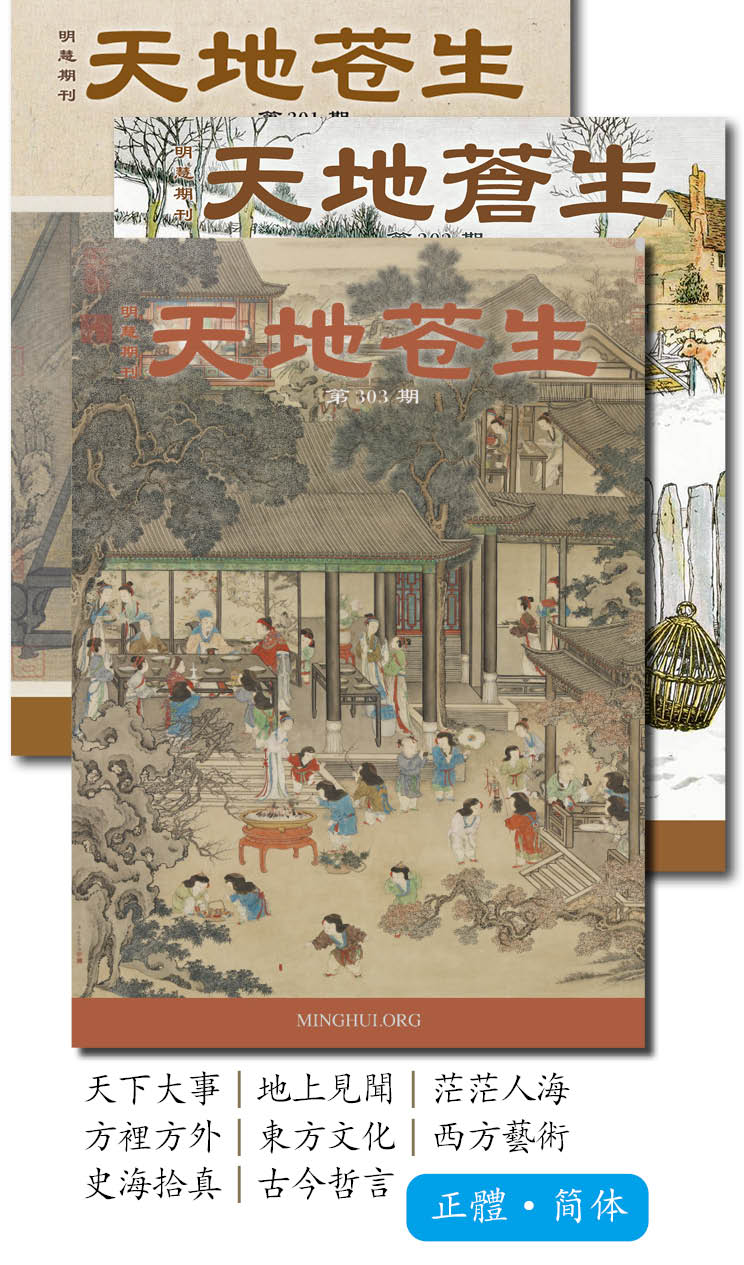走好自己該走的路
當晚打我的惡警值班,我被戴著手銬關在小留置室時又抓進了一些社會人員被關在一門之隔的大留室。打我的警察隔門喊我「你呆著沒事給他們講講法輪功吧。」於是我向他們講真象,第二天早晨警察上班後把我帶到公安局八樓國保大隊,進門打我的惡警向610和肖斌等人介紹說「這是昨天抓的又一個劉胡蘭。」(雖然他們毆打學員,但他們對法輪功和學員是佩服的,自己都說現在的警察都像個流氓似的。)在國保大隊在610和肖斌的指使下自己又遭受了進一步的迫害,在那裏我遭受了「跳芭蕾舞」「拽頭髮」等酷刑。可在家屬詢問情況時610的樸南洙等人還自稱現在決不動手打人了,簡直就是自欺欺人。將來對簿公堂時,每一個受迫害的學員都會指證這些歹徒的惡行。
有一個警察知道我發正念後再也沒有動手打我一下,並用紙巾搽我銬在背後受傷留下的鮮血後站到一邊去了。(他並不是真同情法輪功而是怕自己遭報才不敢動手的。)見問不出啥,又少了一個幫兇,他們就用其他辦法折磨,如拽著頭髮在地上拖或強迫蹲跪在地上,前面用椅子頂住頭部,後面拿一個椅子放在背後兩臂之間抱住,再把手反銬在背後,惡警反覆拉、拽緊手銬,手銬全部銬到肉裏了。(被帶到國保大隊的學員大多數都承受過這種折磨。)
當時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一個惡警打了滿滿一桶冷水從我脖子倒下去,我全身裏外都濕透了,直到4天後家人知道情況後才送來換洗衣服,期間一直穿濕透衣服。同時肖斌(延吉市國保大隊)等派惡警去我家非法抄家(被抓時鑰匙落入惡人手中)。他們在無人的家裏非法搜家,但在師父的保護下惡警並沒找到甚麼線索。
在反覆的折磨後惡警也沒辦法了,只好又把我送回派出所,當晚被送進拘留所。犯人們見我打成這樣,知道是煉法輪功的後都指責警察沒人性,其中一人說:「我算服了法輪功了,不論怎麼折磨就是煉,就是堅持自己的信仰。」我在拘留所除學法煉功外就是給人講真象和學員相互交流。一次我講起在派出所上廁所時因派出所內沒廁所到外邊去了,他們怕跑就讓我到牆邊去方便,當時天漆黑,派出所的牆很高但有一面牆上靠著一架梯子,通過梯子跳牆可以離開魔窟,可是兩次上廁所惡警都不給打開銬在雙手上的手銬。我當時想:雙手戴著手銬怎麼跑啊因此沒跳出去。有一位老學員說「你人的觀念太重了,也許你戴手銬跳出去環境就不一樣了,說不定手銬就銬不住你了!」可是自己當時被人的思想束縛住了就沒有走出這一步才被邪惡進一步迫害。在拘留所明白了真象的管教對法輪功學員另眼看待,非常照顧,並對其他犯人說:你們這些人應該多看看這些人(指法輪功學員),向他們學一學。
在那兒我們也經常發正念鏟除一切迫害自己的另外空間的邪惡,可夢中總是有非常邪惡的東西跟著我,寸步不離。無論走到哪都是不肯離開,我恍惚中悟到和自己有著一種因緣關係。(後來看師父新經文才明白自己也和舊勢力有過簽約,所以才被進一步迫害。)後來被送進臭名昭著的長春黑嘴子女子勞教所。我皮膚上起了許許多多紅疹,痛癢難熬,用手一抓就是一片。後來發展到從頭髮到腳全部連成了一片,被送到勞教所時渾身上下從頭到腳連巴掌大的一塊好皮膚都沒有,皮疹上面長滿了一層白屑,走路都直掉渣(常人稱之為牛皮癬),誰看了誰害怕。剛開始惡人誰都不敢碰,唯恐被傳染上,小隊的管教更是冷嘲熱諷,妄圖藉此誹謗師父,詆毀大法。我當即坦然告訴他們我堅信師父,堅信法輪功,其他的不用說了,對我沒用。後來在沒用一片藥的情況下病業情況逐漸好轉,去勞教所半年多後,在一次小隊會上惡毒的管教又提起這事,並讓我表態,我當即發言說道:「我剛來時不是管教問我煉了法輪功為甚麼還生這種病時我告訴過管教這是我個人的業力所致。今天管教問我為甚麼好了,我就告訴管教,是因為我自己消了業了,所以就好了。」管教無可奈何從此死心,不再強迫我放棄信仰了。大法的法理在自己的身上又一次展現。我剛進勞教所時大夫告知:「要想治病,必須在徹底轉化後才可以,帶到勞教所外看病後在所內治療。」在勞教所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我一方面發正念鏟除我病業背後存在的邪惡因素,另一方面我把自己當作煉功人按照師父講的法理去做。就是這樣,因為痛癢難忍有時也忍不住用指甲使勁抓撓,內衣褲上也被弄的血跡斑斑。一個年齡大的護廊看不過我經常因痛癢不能入睡,告訴我。「乾脆給家裏寫信,讓家人郵些藥來,就別遭這罪了。」我對她的好意一笑了之,就這樣一年多後從勞教所出來時身上乾乾淨淨一身輕。
在勞教所裏堅強不屈的大法學員之間相互鼓勵,互相聲援。由彼此不認識、不熟悉到認識、熟悉,因為彼此對法理的正悟、正信、堅定而感到特別的親,特別的近。這種親近決不是與家人的那種親情,更不是與友人的熟知而感覺近,而是因為我們都是大法弟子,我們都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遭受迫害,都是對師父、對法理堅信不移,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在那種環境下堅強不屈的大法學員被猶大或吸毒賣淫的犯人時刻看守(不屈服的稱為嚴管),但是看得了一個人的身體,卻看不了一個人的心靈。我們的身體雖暫時得不到自由,可我們的心是純潔自由的。往往學員之間的一個眼神,一個會心的微笑,交流完畢。這又怎麼能是邪惡看得了的呢!
而那些在壓力下被迫妥協的和順水推舟的就被迫沒完沒了的反覆看那些攻擊大法的書,幹那些不願幹卻又不敢不幹的事。(不屈服的可以不買攻擊大法的書,而妥協的人必須買,他們精神上也快樂不起來),而真正的邪悟猶大不但助紂為虐,還指使吸毒、賣淫者打罵、侮辱大法學員、甚至親自動手毆打、辱罵、折磨大法學員,簡直就是跳梁小丑。她們協同惡警每天對堅強不屈的大法學員施加各方面的壓力。在我解教前夕大隊長又找到我,告訴我所有不妥協的大法學員解教後不可能回家,必須有當地610來接或過院(送往監獄的意思),讓我寫轉化書後好回家,並說這是唯一最後的機會。我當場拒絕迫害,但自己心裏也有壓力。當時有一個堅強不屈的大法學員就是被全副武裝的當地警察接到當地洗腦班的。當時小隊許多有正念的人為我面臨的處境而擔心,就在我將解教的前幾天家人又千里迢迢來到勞教所告訴我:「勞教所裏往家裏掛電話了,告訴家人因你不轉化解教時必須由家人和當地警察來接,接回去也回不了家。」母親自從我進勞教所後天天吃藥,接到電話後心臟病又加重,並說:『我回不去可能就見不到她最後一面。』並哭著讓我寫一份假決裂及保證好回家。地方上的環境非常不好,西邊磚瓦廠個體戶楊忠芳(大法弟子)被打死,多人打殘,離家出走或勞教等。你好好想一想。」回到小隊後我心裏非常沉重,坐那默默的幹活,感覺好像沒活頭了,沒出路了。怎麼辦呢?真要違心的寫甚麼?那不但對不起師父,對不起法也對不起自己。要不……思想一不正,邪惡就開始鑽空子,腦子裏正胡思亂想時又覺得一切都不對勁,不知不覺中想起了師父的話「正念正行 精進不停 除亂法鬼 善待眾生」(《正神》)。心想如果這樣做了高興的是魔,又怎麼對得起師父為我們所承受的一切呢?也沒做到對自己負責又怎麼能算得上正行呢?正念一出心穩了很多,不管將要面對的是甚麼豁出去了,我是個大法粒子有師在有法在一切都不用我去想,更不用人的私念去打算甚麼,只有走好自己該走的路。
到解教那天一大早護廊就喊我的名字,到勞教所門口後一看家人和一個凍的雙手插在兜裏直哆嗦的陌生人在門口。等我家人介紹才知這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因當地610公安局怕擔責任推到派出所,派出所沒辦法派了一個民警接,而這民警一聽是來接法輪功的也沒敢穿警服,臨時穿了一件便衣坐了火車同我家人一起來了。在回到本市時民警告訴我現在還是嚴打(指迫害法輪功)你還煉嗎?我明白是啥意思,這是師父點化自己不能給邪惡迫害自己的機會和藉口。於是我不斷的發正念鏟除另外空間的邪惡,到當地派出所一看,一個大屋子裏坐了滿滿一屋警察正嚴陣以待呢。當時610的人和警察問我回來還煉不煉了?這時接我的那個警察一個勁的說我表現好等等,那些人也就不多說甚麼啦,就這樣我回到家。到家後一看媽媽瘦了許多,卻笑呵呵的坐那看我,絕不是要不行了的樣。真是難行能行,做到了環境就不一樣了,過後按約定我把消息傳回了勞教所,我身心自由了!出來後環境還挺緊張,經常有特務暗中盯梢,過一兩個月後和一個同修接觸時他們好像對我有所顧忌、防範、不願意交流,更不願把師父的新經文拿給我看。我覺得不對勁,就想我是真修的師父知道就行,該得的我都能得到,這時一個老太太把她手抄的新經文送給我,我知道這是師父在鼓勵我。直到有一天和一位學員交流後聽她說:從你的心性和悟性看你是大法弟子,可A學員為甚麼告訴我們你是特務呢?當時聽了這話心裏不太好受,明明是堂堂正正走過來的卻被認做是特務,於是我回答說:第一也許有邪惡因素的干擾迫害。二是我自己本身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並做了簡單的解釋,但心裏一點也不恨A學員,想也許A學員出發點是為學員安全負責吧。當天晚上做夢,夢見A學員要被壞人迫害跑來向我求助,於是我立即幫A學員脫離了危險。過後一想被學員誤會不誤會都不重要,解釋清楚就行了,不執著其他,每個人背後有師父在管,每人不正的行為師父都會點化的,做正做好此時自己該做的。過後當自己走過這一步時環境又變了,更好更和諧了。
在這段路中自己也有許多怕心、常人心。有許多事情做的並不好,動的念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純正。可是在法的威力下自己就像一個初學走路的孩童有時搖擺;有時跌倒了再爬起來,而師父就像一位慈父,在任何情況下也不離、不棄,引領、鼓勵、看護我這個不精進的弟子使自己在正法這條路上逐漸成熟,同時深切感受到在正法這條路上用常人思想衡量事物和用正念去面對事物動一念是有天壤之別,天地之差的。
以上只是個人修煉路上的一段路程,寫出來只是為了揭露邪惡的迫害行為,將其曝光,而自己也只能在正法路上繼續精進,達到大法對自己的要求標準,做到無私無我,溶於法中才能面對師父的佛恩浩蕩,才能無愧是主佛親身正法時得法修煉正法的大法弟子。